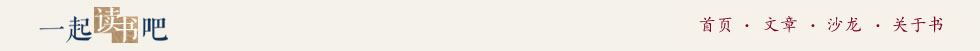A Trap Baited with Pleasure.
瘾品大多属于危险物质,最好是在医生监督下限量使用。这已经是官方对瘾品的社会角色所采取的立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立场。商人、资本家,以及向商人和资本家征税的政治大权在握的执政者很早就发现,瘾品是诱人的产品,也是丰厚税收的来源。由于赚钱的机会和健康的顾虑不能协调一致,精神刺激物的贸易历史中便处处可见因此产生的道德与政治的冲突。自始至终,财政的考虑都与医药的考虑势均力敌。有些瘾品的发展中,财政考虑根本重于医疗。我们首先还是要问,瘾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需求?为什么——这也是保利在300多年前就在研究的——有人为取得瘾品而不惜牺牲一切?
进化的矛盾
瘾品是毒。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植物为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生物碱。昆虫与鸟兽吃了这些植物,会晕眩、辨不清方向,或产生幻觉。然而,有些动物仍然会吃令自己昏醉的植物和发酵的果实,甚至不在意自己的求生能力因而大打折扣。按进化的理论,“意外”吃醉的行为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警告误食者不应再吃这种植物。至于“故意”的行为,不但无益,而且是矛盾的。这样做显然是与自然淘汰的道理背道而驰。
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些是相当危险的。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但转换后是什么状态,并不是全凭瘾品决定的。最终的状态乃是瘾品与服用者的心态、服用者的实际环境及社会处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作用的关键仍在于瘾品。利用瘾品满足转换精神状态的冲动,是不惜接受毒害以得到又强又快的效果。
虽然韦尔假设这种冲动是生来就有的,冲动的强弱却与社会环境大有关系。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被囚禁的动物也远比野外自由的动物更容易去食用麻醉物。其实,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状态。人类本来是小群人结队狩猎、采集,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数人从事农耕,生活在拥挤的、受压迫的、疾病不断的社群里。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克兰认为:“如此逃避‘过得太辛苦的自我’,不惜代价换取解脱重负的幸福感——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再也没有比从这方面着眼,更能深刻了解历史演进的了。”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结果。只有少数有毒的分子(如果这些分子能顺利进入循环系统并且穿越从血液到大脑的障碍)能够模拟或影响脑部的奖励与痛苦的控制中枢之内的神经传导素。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诱发幸福感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非常俭省,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或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近30年来的科学新知虽然激增,研究者仍未完全摸清脑部对各种精神刺激品究竟如何反应。有些瘾品会影响多个神经系统,引起“杂乱”的反应,酒精即是明显的例子。但各种瘾品似乎都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会影响中间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也有强弱的不同。这种原始的神经基质系统是快感的主要传送路径,我们决定做或不做某事的动机也是由此而来。瘾品会刺激这个系统——可能也刺激其他尚未确认的系统,借快感发出“这就对了”的信号。即使像咖啡这样麻醉力轻微的瘾品,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使人兴奋起来。有一项针对护士们喝咖啡的习惯所做的细致研究发现,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自杀率仅有完全不喝咖啡者的1/3。这是极有意思的发现,足以证明瘾品的确是帮助人应对生活的工具。
不过,续杯之前你要记住:反复服用含咖啡因或其他成分的瘾品也会改变脑内本来的化学作用,以致有损健康。脑部不断吸收外来化学物质的同时,会调整内部分泌相同物质或受体的数量,从而对外来的供应产生依赖。这外来的供应一旦中断,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鸦片瘾断毒时引发的多种症状尤其明显,包括烦躁、冒汗、极度焦虑、沮丧、易怒、心慌、失眠、发热、发冷、干呕、猛烈腹泻以及类似感冒的浑身酸痛。严重的痛苦折磨使许多毒瘾者但求一死了事,以下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925年的病例即是一例。
病因:吗啡与优可达(Eukodal,二氢羟基可待因酮)滥用,严重的断毒症状……病人为德国纳粹要员,参与希特勒发动的政变期间受伤住院;据说从医院逃至奥地利,医生施给吗啡后染上毒瘾。进入阿斯普登疗养院之后,出现剧烈的断毒症状(虽然护理人员给他加量服用吗啡,仍无法控制)。期间他变得有攻击性,行为暴烈,不能持续留院休养。曾扬言要自杀,要“死得像个男子汉”、要切腹等等。
曾经获得“蓝徽勋章”(blu Max)的戈林,曾断断续续服用吗啡达20年之久,还曾在德国空军参谋会议上打瞌睡,都证明鸦片类瘾品对人体的影响是多么强。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于1954年从北非的丹吉尔(tangier)写信给诗人金斯堡说:“药房那个人卖了我每天用量的一盒优可达安瓿,他的一脸奸笑仿佛我吃了陷阱上的诱饵似的。艾伦,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瘾头,每20小时打一次。也许因为打的是优可达,这东西是半合成的。要做什么害死人的东西,谁也比不上德国人。”
凡是刺激精神的瘾品,只要养成经常服用的习惯,断瘾时就会出现一些生理与心理的症状。连含咖啡因饮品之类不那么强效的瘾品也不例外。1989年间,伦敦的哈默史密斯医院(Hammersmith Hospital)的医生们发现,病人手术后常见的头疼症状并不是手术中的麻醉引起的,而是因为手术之前与期间不能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所致。除了头疼之外,常见的症状还有情绪低落、困倦、打不起精神。断瘾症状虽然不等于上瘾,研究者却在其中发现“咖啡因成瘾症状”的确凿证据。例如,病人为了喝到咖啡会无所不用其极,会在危险有害的情况下照喝不误,会罔顾损害健康的后果与医生的警告而继续喝。巴尔扎克(Honoéde balzac)即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因坚持不改酷嗜咖啡的习惯,致使死于心脏病的后果提早到来。
人们明知这种行为对健康有害,为什么不愿停止?由“效用逆转”的观念可以看出个中端倪。服用瘾品而上瘾的人——如巴勒斯所说——是掉进了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既然是为了感觉舒服而服用,就恐怕停止服用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上瘾形同劫持人体自然的强化奖励机制,断瘾症状就是抵住脑袋的那把枪。曾经上瘾的人就算彻底戒毒(可卡因之类的瘾品完全戒除干净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时间),也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脑会记得达到快感的化学瘾品快捷方式,生活环境中的细微线索——例如常去的酒馆招牌——都可能挑起强烈的渴望。瘾品上瘾实在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脑部疾病。
接触的机会
人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服食瘾品?瘾品上瘾的根本原因在于脑细胞一再有机会接触瘾品吗?抑或是因为上瘾的人自己的基因、心理、社会、文化、道德上本来就有问题?这个议题与理解瘾品发展史和执行有效的药物管制政策都大有关系。
诸多论点之中的一个极端是精神科医师贝叶罗的一派。他认为,瘾品就像病原体,可借人为的手段诱发任何人的破坏性冲动:“不必有异常人格或潜在的社会问题,人就可以对瘾品上瘾。”关键只在有没有机会接触到瘾品。这个论点可以解释德、美等国医生染上毒瘾的比例为什么从来都高达一般大众的100倍。曾任美国毒品管理局局长的安斯林格说过:“我们简直没见过律师搞这些东西。我可不相信这是因为律师比医生护士更有道德,或是因为律师比较有办法躲掉这种麻烦。这是躲不掉的。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总有人会想试一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管制货源。
另一个极端是斯塔顿·皮尔(stanton Peele)的一派。他认为,瘾品上瘾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瘾品的问题。上瘾和瘾品或瘾品的化学特性无关,赌博等活动也一样会有人上瘾。按这个论点,上瘾者基本上是能力不济或误入歧途的人,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服食瘾品,为的是要“安然沉湎于一种把一切人生难题的意识都泯除的感受”,是个人的价值观在决定要不要服用、是否持续服用、是否成瘾、该不该戒除?而个人价值观是受文化价值影响的。假如文化本身是容忍醉酒的,是让酒有能力左右人的行为的,会发生酗酒问题的比例就一定高于反对醉酒、要求个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文化。因此,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国民平均酒类消费量虽然都很高,爱尔兰的酗酒案例却比意大利普遍。可见症结不在货源,是个人与文化的价值在影响需求与习惯。
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多数的瘾品制造者、销售者、广告促销者的看法)是,以上两个似乎互相抵触的观点都言之有理,但先决条件是人能够受到所接触的瘾品的影响。不论何种瘾品,使用过的人不一定都会上瘾。香烟是可能使人上瘾的瘾品中影响力最强者之一,但试吸过的年轻人只有大约1/3会有烟瘾,有不少人天生就有对某些瘾品免疫的特性。例如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因为对香烟过敏而变成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士;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年轻时之所以没有吸大麻,是因为肺里不能容忍烟进入,即便朋友们一再教他抽,他也没学会这牛津大学学生的基本功夫。对某种瘾品始终会有强烈不适反应的人,等于对上瘾免疫了。意志力强的人,谨守宗教戒规的人,也比较不易去尝试。与上述各类相反的人,爱找刺激的反社会人格者,试用而上瘾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皮尔认为关键在个人是有道理的,但集体的行为也是重要的,例如,土耳其人强烈忌讳吸鸦片(但不反对输出鸦片),因而没有严重的鸦片瘾问题。中国文化把幻觉行为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始终未在中国普及。反观日本人,因为对豪饮采取放任态度,使得半数人口基因里带来的喝酒潮红反应也失去原有的保护作用。
至于和瘾品近水楼台的关系有多大影响,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证据。19世纪的后半期中,伊朗的鸦片生产迅速扩大,当时的丝织业正趋于衰退,鸦片的世界需求量却在渐增,伊朗人因而视鸦片为理想的出口作物。后来鸦片出口也衰退了,许多伊朗人为了排解经济困顿之苦而抽起自种的鸦片。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施扫除鸦片生产的政策,当时估计国内吸鸦片上瘾的人数约为280万。实施扫毒的结果可以预期,毒瘾者减少了,1968年估计约在25万到50万之间,但吸食走私海洛因的人数增加了。继巴列维之后执政的宗教领袖们,想尽办法要消弭邻国走私进来的海洛因。然而,即便发起了反毒运动,吊死了数十名贩卖毒品者,却仍堵不住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入的海洛因。对于诱使伊朗人使用并买卖瘾品的严重失业率,伊朗政府也束手无策。
古巴人曾经有过消耗掉古巴雪茄总产量三成的纪录,亚洲种植并销售鸦片的地区内,抽鸦片上瘾者一向都多于不种、不卖的地区,加纳与尼日利亚等非洲转运点都有严重的海洛因与可卡因毒瘾问题,美国肯塔基州的肺癌比率特别高,这些现象都显示,经常接近瘾品,熟悉且容易取得瘾品,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呢?菲利普·巴里东(Philip baridon)汇集了33个国家官方调查的瘾品上瘾人口比例进行研究,于1973年发表。他在研究中做了多重回归分析(估计相对原因权数的统计学方法),将上瘾比例与社会、经济、地理各方面12种独立因素对照(包括都市化状况、平均国民收入、与鸦片或可卡因产地邻近与否等等)。结果发现,邻近产地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都大,45%的差异与产地邻近与否相关。巴里东因而认定:“在诸多复杂的心理与社会的解释纷争之中,瘾品滥用的最根本的事实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如果不能取得瘾品,就不会有滥用的行为。”
瘾品发展过程的背景中充满白白赠送的促销手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学校迎新活动周赠送香烟和维·马里亚尼酒,短程快速赛车中赠送无烟烟草,过剩的巴西咖啡免运费送到日本,都是实例。100年前的美国工人酒馆换了一个方式:午餐免费,啤酒要付钱。曾有一位芝加哥市的业务员向同事表示,他渐渐发现自己不是为了免费午餐去那家酒馆,而是为了啤酒,所以必须戒掉再去的习惯了。这些赠送手段背后的用意是要给可能成为终身顾客的人更多接触的机会,尤其要抓住消费习惯仍有可塑性的年轻人。受影响度排行榜第一的是年轻、单身、社交活动偏少、欠缺体质上或文化背景上的防范机制、已经在使用其他瘾品的都市男性,这一类人最有可能试用新的瘾品,而且试用后会上瘾。贝叶罗强调,并非仅有这一类人会成为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只要假以时日与充分的接触机会,就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同样的路。1915年间,美国吸香烟的人口大多只限于台球馆和街头路边的范围,到了1955年,美国25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有2/3是老烟枪,其中绝大多数是吸香烟。
上瘾、耐受性、需求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常有人说,上瘾者是不在意价钱的。其实他们和一般消费者一样会考虑价钱,如果瘾品售价涨得太高,上瘾者会去找替代物,或是减量使用,或索性戒掉。不过,鸦片或卡特等物质毕竟和大麦、燕麦不同,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放弃他们不那么渴望的东西。尤其是短期内因断瘾而正在受苦的人特别容易做这种牺牲。
英国作家兼书商威廉·霍恩(William Hone)曾与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于某个夏日傍晚一同在伦敦北区的野地上散步,两人决定都要戒掉吸鼻烟的习惯,在一时冲动之下双双把自己的鼻烟盒从坡顶上扔进有刺的灌木丛里,得意地扬长而去。事后霍恩写道:“于是我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整夜都不好过。第二天早上我又走在那小山坡上,只见兰姆在下面的灌木丛里找东西。他抬头对我笑着说:‘哟,你也是来找鼻烟盒吗?’‘我才不是!’我答道,一面从我的背心口袋掏出纸包捻起一撮鼻烟,‘我在第一家开门的铺子花半便士买了点儿。’”
类似霍恩这种经验——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那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alfred rive)曾经研究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英国人的烟草消费,他发现失业率从2%上升到10%,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足以证明这是无弹性需求。至于国际间的表现,烟草业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还不只守住既有的版图,英美烟草公司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盈利比以往还高。在美国,1928年的经济繁荣期到1932年的衰退期之间烟草类的零售量只有平均每人1美元的下降率,从26.23美元减到25.29美元。《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老板巴伦(c. W. barron)过世后,他的继承人休·班克罗夫特(Hughbancroft)曾经私下对人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他只买了3种股票: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和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他说出这么做的道理:美国人即便负担不起车子也要开车,不该看电影的时候也照样上电影院,为了买香烟几乎什么都可以不要。他说过:“假如你想赚钱,要挑一个可靠的坏习惯。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瘾品也不受流行风影响。这种说法违背我们的直觉,需要解释一下。瘾品的某些品牌和使用模式——例如101毫米长的香烟、可卡因随身吸食包——会流行一阵而后消失,但瘾品本身一旦被普遍接受,都会持续很多世代,瘾品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的。水獭皮帽、蓬蓬裙,以及其他曾经风行一时的东西早已进了博物馆或被人抛诸脑后,瘾品仍在人们的生活中流窜。自古以来,时尚便是从社会上层往下传布,一方面在追逐,另一方面又要摆脱。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急于获得地位的符号,就抄袭上流社会的衣着、装潢、行为模式。高居社会顶层的人很有警觉,自己的社会地位特征一旦被侵犯,就把庸俗化了的作风弃之不用,另外去找别的,这新找到的以后又会被中下阶层抄袭,时尚因此永远在变,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时尚一旦风行起来,也就逐步走向它的末日。”(齐美尔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今所有社会阶层同时受媒体传播新流行趋势影响的情形。但20世纪以前,西方社会的时尚大致都是自上而下的走势。)
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大众。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把他们的银壶银杯束之高阁,原因何在?答案之一是:这些饮品(以及加在饮品里的糖)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过的服饰却没有。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茶商还有其他优势,包括茶的重量轻,而且容易掺假。大多数人以为以假乱真是黑市买卖才有的事,其实20世纪以前世界各地的合法瘾品买卖中掺假与冒牌都是十分普遍的。卖方为了多赚一点儿钱,葡萄酒、烈酒、烟草、巧克力、咖啡、茶、鸦片、大麻,都不免有兑水、掺假、加味、贴假商标的情况,在茶叶上动手脚更是屡见不鲜,伦敦茶铺老板会让华人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以免被怀疑在茶叶中掺入了黑刺李的叶子。消费者明知茶叶掺假,仍旧照买不误,可见茶瘾不小,这也是无弹性需求的又一证明。像霍恩那样受了一夜的断瘾煎熬之后又去买鼻烟的人,是不大可能在质量上有所挑剔的。
消费者并不是人人都像霍恩有这么大的瘾,不过,人人都会对买来使用的瘾品量产生耐受性。持续使用相同剂量却出现效用递减的情形,或是必须增加剂量才能维持原有的效用,都表示耐受性产生了。经常上酒馆买醉的人发现自己得比以前多喝两杯才有醉醺醺的快感,就是对酒精有了耐受性。这是固有的利润促进机制,能增进需求却不增加顾客。多数惯饮的人后来会达到中毒的高耐受量。酒瘾最大的人通常不会超过每天10盎司纯酒精的耐受量,吸烟则以两包(40支香烟)为限。但也有人超过这个限度,罗斯福总统每天抽到4包,著名电影制片人戴维·赛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是5包,演员约翰·韦恩(John Wayne)更高达6包,终于因为变黑的左肺里有个鸡蛋大的肿瘤上了手术台,这时候他抽掉的香烟早已超过100万支。
瘾品是理想商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刺激精神的作用短暂。点燃吸入的瘾品迅速经由肺部进入心脏和大脑,作用又快又强。服下去的瘾品——例如酒与鸦片丸——是逐步进入体内的,作用时间较长。除了LsD、口服美沙酮、脱氧麻黄碱,以及其他少数几种瘾品之外,明显转换意识状态的作用几乎都不超过五六小时。
瘾品的情况和耐久商品是相反的。生产过剩虽然会导致售价下降,却不必担心需求会突然消失。瘾品这类产品本质上就会促使消费者不断掏出钱来,对作用短暂的瘾品上瘾的人更是如此。比约翰·韦恩略逊的一天两包的烟枪,每年大约要吸15万口烟,抽掉1.5万多支香烟,花费——按目前的价格算——1 500美元。从事投资而成为传奇人物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烟草业?制造只用1美分,卖出去可以卖1美元。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有非常强的品牌忠诚度。”
如今的香烟商人如果还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实,那可是在骗人。但早期的烟草业者是否理解瘾品的经济逻辑?他们是否只顾做买卖而不知他们供应的是什么性质的需求?其实欧洲和其他地区普遍有人讲过用了烟草欲罢不能的情形,烟草商当然不会没听过。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在《生与死的历史》(Historia Vitae et Mortis)中写道:“在这时代变得这么普遍的烟草”带给人们“如许的暗喜与满足,所以一旦吸食了,简直割舍不下” 。古人也发现,长期使用鸦片的人可以轻轻松松服下足以使初次服用者丧命的剂量。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于1516年在印度的科钦(cochin)写给国王的信上说:“这是绝佳的商品。经常服用它的人会昏睡糊涂,他们两眼发红,丧失理智。他们服用它是因为它激起淫荡心……这是好商品,消耗量大,价值很高。”早在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和托马斯·特罗特(thomas trotter)说出酗酒是病的观念的150年前,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知道,长期习惯性的饮酒可能“把乐事变成必需”。医生们确知瘾品上瘾是一群相关的神经疾病(如吗啡瘾、可卡因瘾、咖啡因瘾等等)乃是19世纪晚期的事,但走过精神刺激革命早期的人们至少已经初步发现,欲罢不能的使用与耐受性产生的可能性很大,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性交与生意
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个人的苦恼或满足对快感的秘密需求,即便这两种需要也很迫切。他们同样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这也是瘾品很快从无趣的医疗范围向外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近东地区的咖啡馆供给男人们一个外出的最佳借口,让他们在明显缺乏男性宴饮同乐习俗的社会里,有机会和其他男人往来。16世纪的神职人员会反对喝咖啡,不是因为咖啡会引起咖啡兴奋症(marqaha),而是因为疑心咖啡馆是招引男性聚集做坏事的地方。
咖啡馆在欧洲也曾经发挥类似的解放作用,中产阶级渐渐兴起之际,咖啡馆成为供人们闲聊、交换意见、谈论政治、评论艺术的场所。意见的隔阂与社会阶级的界限在咖啡馆里都可以打破,性别的界限却是难以逾越的:17~18世纪的咖啡馆里几乎看不见女性顾客。德国倒有“咖啡集会”(Kaffeekränzchen),这是妇女们自组的聊天活动,集会中可以讨论时事和时尚,这却引来古板人士的挞伐。
大麻和鸦片虽然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无甚贡献,却仍是男性群集休闲之中的要角,和抽烟斗、雪茄相似,香烟更是随时随地的便利交际的工具。在中国,男人们标准的打招呼方式是说:“抽烟吗?”同时一手递过香烟包来。敬烟和请人上酒馆或喝咖啡一样,会增加接触瘾品的机会、增加消费量,终至增加上瘾的人口。折中主义的医生兼药学专家约翰·尤里·劳埃德(John Uri Lloyd)也广泛研究瘾品的历史,他认为,导致“放荡行为”的往往不是瘾品本身,而是借瘾品交往的关系。
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香烟非常彻底地融入20世纪的群居生活,有人会把香烟描述成人的替身。一位在丈夫离家时抽香烟的女士说:“我觉得它就像是个伙伴。”一位打猎时独自在树林里抽香烟的男士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有人陪伴着。”
到了20世纪中叶,尼古丁气味成为浪漫的气息,抽烟也成为男女欢爱行为的一个附件,酒精依然如此,自古就是性爱的助兴物。“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卡罗琳·纳普(caroline Knapp)做过这样的概括,她在酗酒期间打定主意不和喝酒有节制的男人约会。不过,酒精对做爱前戏比较有用,对最终成其好事却未必有益。莎翁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的守门人对麦克德夫(Macduff)说得好:“它会激起欲望,却教你表现失常。”
许多男人用药助兴是为了把高潮的时间延后,过早射精在许多文化之中都是令男性觉得丢脸受挫的毛病。1563年间,葡萄牙属地果阿的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医生加西亚·奥尔塔(Garcīa d’Orta)——死后被宗教法庭判为暗中信奉犹太教——发表了一部有关印度出产药物的著作,其中包括将大麻、曼陀罗花、鸦片当作致幻剂与催情剂使用的论述。鸦片乃是“到处都有大量需求的商品”,人们买来收藏着,小量地食用以排解平常的不适,但也常有人在行房之前服用它。(呼应皮雷斯所说的“激起淫荡心”。)奥尔塔认为这种做法令人费解,因为所有专家都证明经常服用会导致阳痿,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明白事理?“这不是很体面的话题,更何况我们是以葡萄牙文讨论它。”他这么表示之后,又接着用迂回的文辞细谈同步性高潮,“这时候服鸦片就有帮助。它……可辅助较从容地完成性交行为。”
吗啡和可卡因也曾被用来制造这种延缓效果。瑞典人称为“性动力”的安非他明也曾被用于达成同样目的(瑞典俚语中描述瘾品的词十分丰富多彩),有些抗忧郁药也曾经误打误撞成了催情药。一位医生开了氯米帕明(clomipramine)给忧郁症病人服用之后写道:“附带提一下,他的夫人——一位高大的影星型女子——希望他继续服药,因为他维持勃起的时间比从前久得多了。”这又是一个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使用烟草亦然)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男性企图调整一种自然的冲动欲望,用了不自然的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却把原来的本能赶跑了。
比较不易上瘾的致幻瘾品也经常被当作催情剂。利里曾经叱骂不服用迷幻药的人说:“拿你平时做爱的情形和服了LsD以后相比,不管你以为你那样做的快感多么销魂,都像是和百货公司橱窗里的假人做爱……在细心安排的情爱LsD体验过程中,女性能有好几百次的高潮。”古代和现代文化中普遍当作催情药使用的大麻,效用比这个温和得多,但爱用者是一样踊跃的。大麻能解除抑制、增强敏感度,还能扭曲时间感,使高潮显得更持久——这种效用可能因服食者的期望而加强。1980至1981年间,乔治·盖伊医生[George Gay,在海特·阿什伯里免费诊所(Haight-ashbury Free Medical clinic)工作]与同事做了一项独特的研究,对象是120名酷嗜瘾品与热衷性爱的人。研究者与这些人一一对谈,要他们说出各自的偏好有哪些。那是旧金山尚未爆发艾滋病的年代,这些人所说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经验老到的人选出能增进性交快感的瘾品冠军是大麻,领先MDa(此为男同性恋普遍使用的)、可卡因、LsD诸项。
大麻也能增强享用食物与音乐时的快感。曾有一名21岁的学生说:“男生爱女生,性最妙。吸了大麻‘嗨’(high,亢奋)起来,什么都最妙。”大麻这么全面的快感促进功能,不是每一种瘾品都具备的,但是别的瘾品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加乘搭档:葡萄酒配饭菜、咖啡配甜点、喝啤酒配掷飞镖。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现代的广告会刻意宣传瘾品——合法售卖的瘾品——的这类功能,但增进某种快感的功能并不是广告率先说的,也不是广告里一定会说到的,比广告更古老、更有效的是口耳相传:酒馆里的私语、墙角撒尿处的涂鸦,都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在偏离正轨的享乐亚文化之中,瘾品有助取乐的信息传得更快。例如,海洛因可延长性交的说法,最初是在美国东北部各都市中常逛红灯区的年轻男性之间传开的。
有人第一次试用瘾品就会爱上它。吉姆·卡罗尔(Jim carroll)在《篮球日记》(The Basket Diary)之中说:“什么也比不上那第一次的快感。那就像10次的性高潮。”但是,比较常见的初试反应是不喜欢或恶心不适。有时候恶心之中也夹杂着快感,有时候则没有。对于苦味、辛辣的烟,有作呕感都是人体自然的抗拒,也是瘾品畅销上的最大障碍。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只试吸了一次烟草就戒烟了,许多尝试瘾品的人也和她一样,只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他们都遵守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对毒性生物碱警觉避开的原则。
但也有人吃了苦头后不会立刻学乖。这种人会一试再试,主要是因为同伴的鼓动和压力:没关系,每个人第一次都会恶心,下一次你就会知道其中妙处了,要是你老不开窍,可就太逊了。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工人若是竟然不会喝酒,就会被伙伴们讥笑为“krasnaiad evista”(红丫头)、“mokraia kuritsa”(软脚母鸡)、“baba”(乡下女人)——全是阴性名词。真正的男人要会喝酒,也要会抽烟。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在回忆录里写到爱尔兰少年时代的同伴们:“他们不信我不会抽烟。他们以为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好,要不然就是我有肺病。不会抽烟的人哪儿能交上女朋友?”和他同时期的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 )也有同感:“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不会抽烟的高中学生会到处碰壁。”他初次抽烟虽然感觉不好,却强忍着难受继续抽,此后一直抽了30多年。
靠社会问题获利
新出现的瘾品往往要分占既有的瘾品市场。例如,17世纪的金酒竞争,18世纪的咖啡因饮品问世,都曾使荷兰的酿酒业者承受很长的衰退期。在拉丁美洲,大麻被作为使人陶醉的便宜方法传入之后,烈酒也曾进入辛苦的竞争期。在尼日利亚,廉价金酒一旦上市,就取代了价格昂贵的传统待客品可乐果。香烟出现以后更是在烟草市场上一枝独秀。以1900年的美国吸烟者计算,平均每吸两支雪茄才吸一支香烟;到了1949年,香烟与雪茄的比例变成65∶1。1899年上市畅销的阿司匹林是鸦片类药剂的安全替代品,在1914年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最普遍的镇痛剂之一,医生用药导致的吗啡上瘾也因而减少了。在此同期,奴佛卡因(novocaine)与其他药物合成的麻醉药,几乎完全接收了危险性较高的可卡因原来占有的市场。
瘾品市场并不是论较输赢、你死我活的赌局。新出现的瘾品添加到既有的瘾品之中而加强其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了可乐类饮料以后,喝私酿酒的人可以用它加味,嚼食卡特的人可以用它解酒。镇静剂和巴比妥酸盐可以加强酒精的作用,尼古丁可以加强大麻和卡特的效果。注射海洛因若是加上可卡因,刺激性更强,瑞士人称之为“鸡尾酒”,美国人叫它“快速球”(speedball)。酒精本来是多功能的医药用品,加上新研发的合成物质,又成了新药,在掺有麻醉剂的成药与萜海洛因(terp-Heroin,呼吸系统的抗痉挛剂)之类的医生处方药之中都少不了。制药公司发现,减肥药和其他安非他明类产品加入巴比妥酸盐,作用可以增强;服了添加巴比妥酸盐的产品会觉得心情更愉快放松。
烟草类和大麻烟很适合互相搭配。凡是已经盛行吸烟与吸大麻的文化之中,都有人将两者合用,在摩洛哥叫作“kif”(昏倦),在牙买加叫作“spliffs”(大麻烟卷),在美国是“blunts”(钝器)。烟草产品是大麻走上发达之路的大门,如果没有香烟革命在先,美国的大麻烟文化情结不会兴起那么快、传播那么广。反主流文化的老生常谈虽然说大麻烟是烈酒的良性替代品,酒瘾大的人却很可能兼有大麻瘾。总之,抽香烟与饮酒已经使大麻烟和其他瘾品的需求增加了,并没有使之减少。
瘾品常可用于抵消其他瘾品的作用。巴比妥酸盐类和古柯酒都可以减轻鸦片类药剂的断药症状。镇静剂、鸦片类药剂、烈酒都可以缓和可卡因的药力。咖啡豆和可乐果都可以用来解酒。吗啡和海洛因亦然: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许多鸦片类药剂的上瘾者起初是为了消除宿醉而开始使用。无酒精饮料的销售者也会把其产品当作良性的另类选择来促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有这样的广告:“宿醉难消吗?来喝可口可乐。”日本三井制药厂推出的“康复”是一种含咖啡因和维生素的口服液,目标瞄准的也是清酒灌多了的人们。
这些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出乎预期的效果,这些效果产生的损失与利润都不是瘾品本身包含的。瘾品的伤害性所引发的外部性向来很多,例如意外事故、中毒致死等等。因此瘾品在19~20世纪受到的管制越来越严。然而,精神刺激革命也制造了许多带来利益的外在事物。各种瘾品问世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精致烟斗、镶宝石的鼻烟盒、细瓷茶杯、艺术茶匙、大麻烟枪、加味卷烟纸等不胜枚举的相关产品。[美国禁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只按香烟纸销售量来估算国内的大麻烟消耗量。]瘾品的确能引发人们的巧思,以往卖荔枝干和煤炭球的人曾经生意兴隆,因为荔枝干可以用来揉鸦片团,炭球便利点燃鸦片烟枪。1876年间,单是伦敦这一个都市,就有30家制造并进口海泡石烟斗的商店。在君士坦丁堡,贵妇名媛们流行佩戴遮掩袖珍型皮下注射器的珠宝。100年后的美国瘾品爱好者喜欢戴安眠酮(Quaalude)药片形状的金坠子和耳环。
“外部性”往往以“问题导致获利”的形态出现,例如瘾品滥用引来的问题可以转变成为提供治疗的业者获利的机会。在20世纪30年代,“消化汽水”(bromo-seltzer,含溴化钾、乙酰苯胺、咖啡因、柠檬酸,无须医生处方即可买到)的销售者发现,买主大多数是想要消除宿醉的低收入男性,因而立刻收回广告,改用星期天的报纸漫画版来促销,因为星期天是“消化汽水使用量最多的日子”。营销“碱性汽水”(alka-seltzer)的对手商家不甘示弱,也针对又抽烟又爱过量喝酒的男性设计了漫画广告。止咳含片的广告印在纸板火柴包装上:“使你喉咙舒爽,口气清香。”
意外收获最大的是调理瘾品滥用后果与帮助正在努力戒除者的医疗系统,后者在美国的获利之大尤其居全世界之冠。19世纪晚期开始成形的疗养业,只是五花八门的邮购疗方和一些私人开设的疗养院(上流社会俚语称这种地方是“浸泡坊”),到20世纪晚期已经发展成为化学品依赖现象的庞大综合体。美国1992年治疗酒精及其他瘾品滥用的花费已经超过60亿美元,另外还有30亿美元耗费在预防、人员训练、研究、保险事务各方面。20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在药物滥用管理部纽约州分处(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工作的人士,他在研究曾经有过药物成瘾的案例。我对他讲起我要撰写美国市井阶层的麻醉药物服用历史,并且要从记录年长的美沙酮病人案例着手,他说我的计划很好,不过有一点很可惜,因为我漏掉了真正的主戏——药物成瘾治疗产业。
这产业商机之大,连他也始料未及。其实问题导致获利并不是瘾品发展中独特的现象,凡是利用人类本能冲动而起家的企业中都有。人类始祖的进化本来是为了适应脂肪和糖类都稀少的非洲大草原的生活。谁若是能在难得的可以大量摄取脂肪的时候饱餐一顿,才有可能在遇上饥荒时保住小命。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仍然保留种种此类本能冲动,即便在如今的快餐社会里,这种本能已经变成健康上的劣势,却还是容易被利用的弱点。自从哥伦布来到新大陆,新食品的汇集与口味发展都与瘾品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与新大陆的接触,现在也不会有巧克力糖、比萨酱、爆米花、炸薯条(美国境内的马铃薯每3个之中就有1个成了炸薯条)。到了1997年,美国食品加工业每年运到国外的薯条重达38.6万吨,麦当劳(每天喂饱美国7%的人口)在105个国家设立的分店达到1万家,单单日本境内就有2 000家。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从远在北极圈稍南的芬兰的罗凡尼米(rovaniemi)一直到新西兰最南的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都可以买到(两地相距两万多公里)。同时期“肯德基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的生意也做到了埃及狮身人面像的脚下,而它在10年前——1987年——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的对面开设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分店。
这些通俗事物到处长驱直入,是有其超越文化界线的生物性基础的。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历史学者苏珊·斯皮克(susan speaker)认为:“资本主义和医药界获利并不只因为我们原本有嗜好高热量食品与精神刺激物的生理倾向,也因为人类各式各样的身、心、灵苦恼是无所不在的。”人类为这些获利付出的代价各有不同。天生就有旺盛的脂肪储存基因的人,或生活在运动贫乏的自动化环境中的人,如果饮食过量,往往招致糖尿病之类的麻烦疾病。美国人可以从平均体重的数据看出来,管住自己不吃过量的食物是很难的,在我们本能的口腹欲望之外,还有商家广告的火上浇油,使我们的理智判断和意志力败下阵来。演化医学专家伦道夫·内瑟(randolph Nesse)和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说:“人类千百年来努力要创造一个真正流出蜜与奶的环境,结果却发现许多现代病和过早死亡都该归咎于这个创造出来的成果。真是莫大的反讽。”
虽然反讽,也让胰岛素、动脉引流、抽脂手术、减肥药丸、跑步机、减肥餐的供应者赚到了钱。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评论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尖锐地指出,减肥是最炉火纯青的消费行为。
瘾品制造者当然也把握了借脂肪赚钱的机会。时装模特儿很早就发现安非他明可以帮人变瘦,英国模特儿琼·道内(Jean Dawnay)说,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模特儿除了安非他明、右旋安非他明、不加糖与牛奶的咖啡之外,什么都不吃,“她们苗条得不可思议,教我自叹弗如。”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为了模仿高级时尚界那种幽灵似的形象,以香烟为减肥的秘密武器,借抽烟来抑制对甜食的欲望。女星安迪·麦克道尔(andie MacDowell)从影前曾是模特儿,靠服食减肥药丸和可卡因保持身材细瘦,她说:“你如果查字典就知道,‘模特儿’(model)的意思是‘范例’。少女们为了要像模特儿那么瘦,什么方法都会试,一天到晚只喝健怡可乐,还有抽烟。”还有比这样更糟的。男影星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说:“有些实际的问题是海洛因和可卡因可以解决的,例如体重过重,或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他是过来人,说得应该没错。
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托马斯·默顿修士(thomas Merton)在1948年间就说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用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这话说得完全对。瘾品制造者与多巴胺的关系就如同色情业者与睾丸素酮、食品销售者与味蕾、整形外科医生与异性追求的美丽外表的关系。这些人都以利益为目标,都能借科技之助启动人体内在的奖励和调节机制。这些机制是在与现今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完成进化的,如此被牟利者利用,显然对生理上有害,在道德上也是一种颠覆。如何处理“靠社会问题获利”,是出现过多次的政治上的两难,在全球化逐渐形成之际,问题也更趋迫切。
摘自《上瘾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