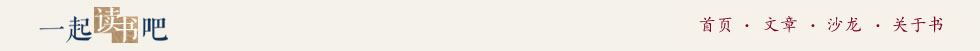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
 假期快到了,你有没有旅行的计划,在旅行的路途上,你会带一本什么书,还是发呆看着窗外变换的景色,或者呼呼大睡? 今天观点君跟你分享张翠荣的新书,来自理想国的《另一片海》。她是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这次,张翠容行走于事件现场,跨越地中海两岸,亲访希腊、西班牙、埃及与突尼斯,以一种在地而全面的观点,探索这一场接一场如推倒骨牌般为民主与经济、自由与尊严抗争的觉醒运动浪潮,试图为读者呈现事件的真相,并提出更宽广的思维角度。 旅程结束,也是开始 文/张翠荣 我第一次真正进行国际采访,竟然就是受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所启发。 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es’Gaze),直望至巴尔干半岛的悲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它不单是欧洲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属于我们的悲剧。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大导演以镜头的凝望介入世界,那么,记者呢?看完《尤利西斯的凝望》,我不禁自问,可否给我一个凝望世界的机会,而且直至灵魂最深处。 我毅然背起行囊,开展我的采访旅程,正如安哲罗普洛斯说的,把观众/读者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在此,容我多加一句:思考未曾真正思考过的问题。而我第一次踏足烽火之地,竟然也是巴尔干,1999年的科索沃。 自此,我一直以旅行采访的方式,希望深入是非之地或争议的现场,把为人所忽略、误读甚至主流媒体以外的故事,带给读者。可是,我没有受雇于任何大媒体,就以自由身的身份,背着背囊,孤身奔赴各新闻热点以及受冷待的地方。这意味着旅途上一切事宜(包括经费)都得靠自己一人打点,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国际新闻的第一线记者多风险,但大媒体的全职记者至少还有较多的紧急援助管道,而作为独立的自由记者,遭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自行设法解决,有时需要机警,有时需要拿出勇气,危险加身时则必须夺命狂奔。 有一次,当我告诉一位生活优越的友人,我如何在物资缺乏下独自完成我的旅行采访时,她惊讶之余,希望我也能与年轻人分享面对逆境的经验。近年有不少励志的书籍涌现,都是企图为那些处于人生低潮或遭逢不幸的朋友,点燃一盏明灯,而书中所描述的逆境,大多不是主观意愿所造成。可是,我的“逆境”却可算是“自作自受”。我想,没有太多人会相信我经常自费出外采访,浪漫背后原来是沉重的代价。 香港传媒很少派记者参与国际新闻现场报道,外国传媒不会看上华人记者,除非是与华人黑社会有关的国际瞩目的跨国犯罪事件,例如人蛇偷运等。结果,为求满足对这世界的好奇心,唯一的方法便是“贵客自付”。 我向友人笑说,做一个背囊旅客已够艰苦,再加上繁复的采访工作,真是难上加难,我姑且称此类记者为“背囊记者”。但我更喜欢称为“独立记者”。 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就这样,独立记者在紧绌的资源下,带着一腔热诚和理想飞向广阔的天空。 在踏上征途之前,我会一如其他背囊旅客,首先收集有关目的地的基本资料:衣、食、住、行,特别在住宿方面,必须在预算之内,以确保不会超支。换言之,在旅途上,我也得是一位善于理财的管家。与此同时,我还得好好准备采访的工作,例如阅读大量的历史背景材料,时刻留意新闻事态进展,以及安排访问事宜和进行有关联系等。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为文章寻找发表的地方。我曾为以意大利罗马作基地的IPS(Inter Press Service)撰写文章,这个通讯社强调雇请当地记者报道当地事务,推动新闻角度多元化,并较倾向同情第三世界,被视作为第三世界发言的最大通讯社。而我则以亚洲人采访亚洲事务为理据,开始为IPS跑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也曾替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中国香港、欧洲和中亚事务,后来集中向大陆和港台报刊供稿。只是,当中不无挫折。 国际新闻,浩瀚如烟,但对不少香港编辑而言,他们只找一个角度,就是寻找与华人有关的故事。在此,我想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99年10月我在某报专栏报道了有华裔血统的东帝汶独立派领袖黎发芳来港访问的消息,由于他的华人背景,香港某周刊记者表示有兴趣做一个专访,我建议她参加由黎发芳主讲的研讨会,会后留步再与他进行个人访问,怎知研讨会还未完结,该记者与同行的摄影记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该周刊记者解释,她看到黎发芳肤色黑黑的,外貌像印度人多于华人,便打消了访问的念头,她还强调说:“要知道,我们周刊只对华人有兴趣,这包括连外貌也要是十足华人模样的。”这种褊狭的新闻态度,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这类让我沮丧的经验和遭遇,俯拾皆是。 早在1994年,一位古巴朋友来信表示,可以应我要求安排专访他们的总统卡斯特罗,这个要求是我在1991年采访古巴时提出的。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第一代革命家,又是美洲国家中唯一的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与美国对抗的具争议性国际级人物,卡斯特罗如何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应是国际关注的新闻素材。“这是你的兴趣,与华人有何关联?请先去采访部问问同事们,有谁认识他?如果有三个以上,我准许你到古巴采访卡斯特罗。”总编辑如此这般对我说,语气中带着无奈。结果,没有一个同事准确答出卡斯特罗是古巴的总统,他们倒有兴趣知道古巴在世界地图上的地理位置。 后来,我又向总编辑建议,在周刊内推介一本非常特别的日记,当时为1994年年初,一位年仅十一岁的波斯尼亚女童Zlata,成功逃到美国,把她在萨拉热窝写下的日记结集出书,名为Zlata’s Diary,日记里呈现了孩童眼中的战争世界,从家庭到学校、从邻家的小狗到军人叔叔,动乱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惶恐里不失天真。总编辑很快把书退回给我,一脸严肃,说:“谁会知道萨拉热窝在哪里?会有共鸣吗?”这或许是对的,波斯尼亚战事在华人的经验中牵动不起一丝涟漪,正所谓: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华人新闻观点,大概就是从华人的利益角度去看问题,凡是与华人利益无关的,便不需要深究了。我想,这种看法,至少在香港新闻界中,是一种主流。至于台湾传媒的国际新闻版,除了华人角度外,便是美国角度了。因此,当北约于1999年3月底展开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我计划前往巴尔干地区采访,本来是一腔热情向某大报国际版编辑提出以日记形式,撰稿报道战事情况,谁料该编辑以冷淡的态度回应:“我们每天所收到的相关新闻电讯稿件,犹如排山倒海,我想,即使你亲临现场,也不会比外国通讯社做得更好。”一盆冷水从头淋下。对该编辑而言,科索沃问题是属于欧洲的,国际版编辑的角色就是翻译外电,干吗自找麻烦安插额外稿件呢,何况还要支出稿费! 《香港经济日报》副刊主编对我的处境有点同情,安慰说:“如果我是老板,一定会采用你的稿件,但现在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只要你能在该地区找一些华人故事,便可在副刊刊登。”我终于为我的稿件在香港传媒找到了第一个发表地,并且取得相对合理的稿酬,算是异数!在我的采访中,也由此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华人故事。 这些华人故事存在于主流国际新闻的边缘,却是香港传媒了解世界的动力,这即是说:我们可能对中东的宗教纠纷表现冷漠,但对处于狭缝中挣扎的当地华人表示关心,也由此对那些华人所身处的社会,有多一点的认识;印尼亦是其中一个好例子,如果不是发生1998年5月暴动,华人妇女惨被奸杀,我们亦不会太留意印尼的民主进程。只可惜,当香港传媒乃至其他中文传媒发现,互联网上所刊载的妇女受虐杀图片原来大部分为东帝汶妇女之后,却没有把焦点放在东帝汶。 这就是所谓的华人角度!角度决定了故事的取舍,以及优先的次序,同时也反映着关注的焦点。那么,华人的新闻观点又是如何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经常强调亚洲价值观,而亚洲的新闻界亦开始酝酿带出新闻报道中的亚洲观点,以抗衡西方观点,而中国大陆也把“中国观点”挂在口边,第三世界国家则指出第三世界观点的重要性。至于“西方观点”又如何?坦白说,西方观点即指美国观点。毫无疑问,我们所指的观点,除了牵涉利益角度外,也包含价值判断。 在此,我们可能应当返回新闻学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新闻应否有观点?在中国大陆,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所共知,新闻的角度当然要反映党和政府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世界护舰的美国传媒,对于国内的新闻事件以至政府的国内政策,可以呱啦呱啦,态度十分尖锐,但一触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却似乎要统一口径,例如美国在中南美洲的角色、波斯湾战争、北约的“人道干预”。记得1999年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接受一项广播新闻训练课程时,导师指出报道海外新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并明确写在采访守则内。因此,当我们谈论新闻观点,其实就是利益价值的判断,美国观点就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欧洲观点就是欧洲利益出发、中国观点就是从中国利益出发,如此而已。 国际级(或国家级)的报纸杂志指派驻海外的记者,也就必须要合乎他们所谓“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因不同机构而定。正由于此,他们大多只会在总部调派“自己人”担当海外办事处的负责人,很少聘用当地人坐上这位置。这说明一点,观点是主观的,明显与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相违背,至少太强调观点,新闻真相难以呈现出来,充其量只是按某一利益价值重新塑造事件的表象,甚至简单化事件而已。 我经常在想,简单化事情本质的企图,是一种对历史的失忆,又或逃避,逃避历史的杀伤力,然后再用某一种价值观的美丽外衣包装起来,去合理化、去让人相信,这姑且称之为“隐藏的议程”(请参考John Pilger,Hidden Agendas)。其实,记者的职责就是把这些隐藏的议程挖掘出来,拨开云雾,让读者更贴近真相,无需执著于华人的观点,或是美国的观点。 当中文传媒工作者关心华人处境之余,也关心世界,跑到前线,掌握真相,诠释真相。这样才可以有我们的分析,有我们的思考。在此,我想起一位知名的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报道迥异于官方媒体,以人性的角度出发,不带任何预设的观点,不作主观的判断,他只对人、事、物静静观察,采取抽离的态度。他曾说过: 当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我通常都很审慎,几乎不错过任何一个记者会,但是我从来不问问题,情愿让别人去问那些问题。有时,我会在一些城镇走上一整天,但决不主动与别人交谈,我只是去看、去听、去感觉。在一般情况下,我宁愿让别人来与我谈话,这由于我不想去强迫或改变外间的情况,对方也许会说一些话,也许什么都不说,不过这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因为他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 卡普钦斯基的采访手法明显与那些西方明星记者不一样,他不会提出尖锐难缠的问题,也不会只顾埋首奋笔疾书记录答案,他相信只要用眼睛和心去看,就能看清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他的作风虽然不符合西方新闻工作者的标准,但具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并且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堪称新闻工作者的典范。事实上,他冷静客观而又富浓厚人文色彩的报道,已令他在国际上享负盛名。他在萨尔瓦多的一篇报道,一篇有关该地早期游击队领袖哥梅兹遭枪决的经过,一如其标题:“让我们看,让我们思考”。如果采访要有角度的话,那就是广阔的人文关怀胸襟,一针见血地抓到问题的核心,让读者看,让读者思考。 因此,我无意去弄什么“东方观点”或“华人观点”,如果记者需要有观点去理解新闻的来龙去脉的话,我希望将一切都归零到“人的观点”,而且没有预设立场,即使有,也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立场。如是者,欧美的新闻机构虽然财雄势大,他们永远都有一大堆记者在外头跑;可是,那些自由身记者,自告奋勇,跑遍各地,他们好像很清楚该到什么地方去,当世界上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他们都会在现场采访,报道第一,报酬第二。少了一重束缚,多了一份自由,而他们的报道比大机构记者往往来得有角度。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想,对世界的好奇心会很容易推使一个人当上记者,一旦当上记者,就好像学者追寻学问,都会变得锲而不舍,在所不计。一如卡普钦斯基,还有其他的驻外记者,踏尽天涯路,跻身于无数的新闻风景中心,只担当旁观者,是不是有点不道德?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脑海出现,特别是人在旅途中时。“我为什么而来?”当我迷失于旅途上,那是最好的抚心自问。 美国知名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便曾在战乱时期多次探访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并在当地上演法国剧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引来外界议论纷纷。桑塔格解释说,由于在数次的探访中,她对于这个饱受蹂躏的城市和她所代表的一切,产生了热切的关怀。她表示:“我不能再次成为一个目击者,只是会面、探访、怕得发抖、感到勇敢、觉得颓丧、参与令人心酸的谈话、变得更愤怒、体重减轻。如果我再回去,应该是投入去做一些事情。”因此,桑塔选择了文学和剧场,她相信当地人会因为他们的现实感受被艺术所确认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而感到坚强及安慰。“文化,在任何地方的严肃文化,都是人类尊严的表达。”桑塔如是说。 结果,戈多先生的信差来到,至于戈多先生呢?信差重复再重复一个似乎永不兑现的口讯:明天会来吧!台上的表演者听后开始落泪,台下观众默言无语,有人跟着啜泣。剧场外来了一阵枪击声,坦克在街上隆隆驶过。这幅景象一直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作家选择“投入去做一些事情”,那记者又可以做些什么? 直到1999年4月,前南斯拉夫的另一块土地科索沃再向世人展示仇恨的血腥,北约空袭南斯拉夫;在香港这边,正好在国际电影节中上演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一系列巴尔干电影,其中《尤利西斯的凝望》以最丰富的电影艺术语言,勾画出一个地区和一个时代的不幸。片中主角为了寻找先人失落了的电影胶卷,走遍巴尔干地区,从罗马尼亚到波斯尼亚,亲身经历阻隔,目睹流徙与战火。正如安哲罗普洛斯向外界表示:“所有的电影都是全新的旅程,每回我动身踏上电影之旅,都学到或看见未亲自接触过的东西。但这些旅程,穿越历史、穿越地貌,也拥抱从爱欲到仇恨和战争等人类情感。”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触动观众已死的感觉,我想,这是由于人类原本是一个大家庭,拥有共同的感情,艺术让我们更为贴近。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向我说,如果想写作有进步,请多看电影。我认为,无论电影还是文学,都是记者必修的感性之旅,亦是新闻触角的启发源头。正由于有了桑塔格和安哲罗普洛斯的作品,巴尔干半岛变得不再遥远了。1999年5月,当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际,我毅然抛开近乎泛滥的外电报道,亲往巴尔干看个究竟,只希望让读者可以一如亲临现场观察,纵横交错地了解这一个陌生地区的遭遇。 一个记者的任务,也是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将消息和其复杂的背景说出去。记者不是医生,也不是社工,更不是救世主;能做到的,就是让人知道,让人思考。东帝汶自1975年以来所发生的暴行,世人一直所知不详;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千名记者挤在西贡采访越战时,却让隔壁的柬埔寨战事偷偷进行;埃塞俄比亚发生严重饥荒之始,只有丁布尔比(J. Dimbleby)报道,以致令他质问:记者同僚,你们去了哪里? 记者要能跑,也要愿意跑,并要有洞烛先机的本领,这就是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波兰同行面对卡普钦斯基,便经常慨叹:“真要命,不知他现在又到哪个地方去了?”事实上,卡普钦斯基曾这样说过:“我必须要旅行,这是我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方式,只有在路上,我的脑筋才会转动,一旦坐下来,我的脑袋就变得一片空白。” 《远东经济评论》的东南亚特派员奈特•塞耶(Nate Thayer),入行之初,原来亦只是身无一文的背囊记者。某天突发奇想,辞掉工作,向妈妈借了一万五千美元,背上背囊,跑到泰国曼谷开始尝试记者的生涯,以自由撰稿性质为多家报纸作东南亚报道。塞耶的足迹遍及东南亚蛮荒之地,其中花了不少时间在泰柬边境和柬越边境,进行高风险的采访,在鬼门关外走过十六次,曾经历严重疟疾、脑膜炎、断骨和烧伤,不知是不是因为他那惊人的意志力,最后竟然又生存过来;并且成为红色高棉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中间人,让他得以把隐没了十八年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带到读者面前,报道了他在隐蔽丛林里所受到的“文革式”人民公审,直到最后他的逝世,都一一作出独家报道,重新唤醒世人本已遗忘掉的记忆,一宗令人类、历史蒙羞的暴行悲剧。 塞耶的报道让事件客观伫立,不再暗晦不明,同时也展示出,在他疯狂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对职责的承担,在困苦中有所关切、悲恻和不安。对我而言,旅程经常会改变既定的认知,它犹如让我看见灿烂火光之际,也听见其中惨叫呼号的声音,还有火光的背后,原来是一幅国际政治的诡秘图像。 为什么东帝汶的故事一直被埋藏于传媒的报道之中?柬埔寨战事为何受到忽视?美国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采取间歇性轰炸的“低调攻击”下的伊拉克老百姓,又如何成为 “Unpeople”(引不起关注的人群)?当一位记者拿起笔来报道这一切,他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一种“介入”,只是介入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些人永远质疑记者的工作,但我相信,记者自有改变世界的角色。而旅程往往让记者在“正常”报道以外,发掘出一些人和事,一些有关在狂暴地挣扎生存过后,等待新生的Unpeople’s Story,正是这些故事,为记者和读者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原来,一段旅程的终结竟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说:“这趟旅行的开始,我很天真,我不知道答案会不会在一个人继续旅行的时候消失,还是随着旅行继续只会更加复杂,而且还有更多的相互关联,以及更多的问题。”就这样,我探索世界的旅程没法停下来。从东南亚的民主进程,到南亚的派系冲突、西方眼中的“邪恶轴心”阿富汗和伊朗,再走进烽火不断的中东地区,然后南下采访拉丁美洲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并分别写成多本著作;直到2011年,我有机会再回到欧洲,这次是沿着地中海的南欧国家,在此之前我已多番探访过其对岸的突尼斯和埃及,北非革命的爆发点。 想不到,在希腊首都雅典,1999年我曾访寻的安哲罗普洛斯,十二年之后,我终于与他相遇,他当时忙于拍摄新作《另一片海》(The Other Sea),他对2008年金融海啸所掀起的地中海波涛,另有一番思考。可惜的是,新作未完他却碰上交通意外,永别尘世,留下茫茫一片大海。人们如失方向,继续拷问,春去冬来,一片寒意;远方,如雾迷蒙。我在迷雾中游走,凝望另一片海,坚持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报道观察,这关乎地中海,也关乎我们在全球化下的共同体。 虽然金融海啸已过了一段时间,但即使到了2014年,问题仍在;欧美无法放弃量化宽松,欧盟更要加大之。是经济,亦是政治;不过,我所关注的,还有平民百姓在危机中如何度过每一天。在主流媒体论述之外,那些 “Unpeople”的故事,他们或气馁认命,或不甘心,又或深切反省,民主与自由,跟着振臂一呼,但那一片海里暗流涌动,仍然一波波推进,冲向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相信不至于隔岸犹唱后庭花吧! 在纷扰的时代,我经常警惕自己,独立记者跨过几许困难,坚守作出独立的记录和书写,更见重要。在孤独身影的背后,不乏后来者。正如钱穆所说: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一起读书吧Vol.515 | 另一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