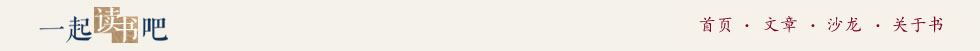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
 5月15日晚,颜歌携新书《平乐镇故事》在北大与读者见面,并请来了带病参加活动的青年女作家七堇年,本次活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主办。 颜歌1984年出生于四川郫县。迄今为止,她出版了包括《我们家》《五月女王》在内的十本小说。颜歌注重写作时对四川方言的加工杂糅,在作家阿来看来,颜歌确实为地域文学、四川地域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方言是一个壳子,一个承载思想的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是颜歌突破了这种限制。以下为部分实录:
 作家七堇年 摄影/杨公振 七堇年: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们聚到这儿是为了颜歌的新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看到了成都姑娘的贤慧与体贴。我跟颜歌是很多年的朋友,内向如我,作者朋友一直不多,颜歌真的是我最熟悉的老朋友。 这已经是颜歌的第11本书了。我们这一代很无奈地被贴上“青春作家”标签的人,经常遇到的一句话,也是很诚恳的,就是读者站起来说“我们是看你的书长大的”。跟颜歌接触这么久以来,她曾经跟我说过,在她的每一本书当中,她都会挑战新的任务,或者尝试在这本书中完成一个新的技巧的练习。从最早的《异兽志》《五月女王》《声音乐团》《我们家》,再到这一本《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我想问她在这本书当中挑战的是什么样的新任务? 颜歌:既然你已经问了,我肯定要回答。我是一个书呆子,所以我的每一本书,我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当成是一个研究项目,在每一本书里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进展。这本书的项目是什么呢?我的上一本书叫《我们家》,主角也是在这个虚构的平乐镇上。在这个平乐镇上的中年的豆瓣厂的老板。这个老板没有什么学识,就是很粗鲁的有钱的小地方的人,他包二奶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是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个性特征非常明显的人。他讲话的特征也是很明显。这个老板讲话就是满嘴都是脏话,各种各样的骂人。之前我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方言的特色或者是小说的语言特色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看过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对这个很有印象。 写了《我们家》以后,回头看看这个小说里的语言特点,现在把它叫做四川方言或者是四川地区的人们的语言特点。它得以这样的强化,其实是得益于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讲话爆粗口的人。所以我的问题是当我们不能讲话爆粗口的时候,四川地区的人的方言特点,以及在这个生态里的人的讲话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我试想研究一些更多的关于语言本身的东西,而不是从人物角色的性格上面占便宜。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面的《白马》是之前写的,后续的四个故事都是女人。这个小说里面的主角全部都是女人。我希望人为的创造出一种日常的非极端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里实验语言,我现在想要拓展的这种语言。因为一般普遍而言,女生骂脏话的比较少。这个小说里面,通俗地来讲,就是在怎么不骂脏话的情况下说话。 七堇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从《我们家》开始,颜歌就一直在探索越来越清晰的方向和风格。就是以她家乡成都郊区的郫县为背景。 颜歌:她一看就是不做饭的,做饭的人都知道郫县豆瓣。 七堇年: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四川的同学,提起来郫县豆瓣也是口水直流的。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方言写作。 我选一篇比较喜欢的,请颜歌用四川方言为大家演绎一下。选一篇比较有特点的,我觉得是《江西巷的唐宝珍》。 这是我相当喜欢的一篇,它的开场几乎像一部电影,可视化很强。大家可以听一听颜歌的演绎。 颜歌:谢谢你们,此处应有掌声。 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是怎样的,我就给大家念一段。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一直想好了要写一个女人,一个小镇上的离了婚的中年女人的婚恋史。这个故事就是在无脏话的环境里还原出四川的风情。当时我的想法是让语言变得更加的音律化、快板化和歌谣化。第一段是我在这方面做的很大的尝试。我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故事的开头。故事叫做《江西巷的唐宝珍》。 七堇年:大家能够听懂吗?四川话是属于北方方言。 颜歌:这是我们四川人自己的看法。 |用心写方言|
 作家颜歌 摄影/杨公振 七堇年:采用方言写作,你曾经担心过吗?比如选择这样的方言写作,会不会排斥一部分读者的理解?或者外地人能不能领会到? 颜歌:我刚刚用四川话念的时候,如果是四川的朋友,你会发现这个四川话有一点点普通话,不完全是四川话。我会做一些处理,我会选择。我觉得用四川话写作的原因,或者是用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写作的原因不是为了把门关起来只让四川的人或者是会四川话的人看,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语言本身的内涵和丰富性。我会进行一些选择。 举一个例子,四川话里有一些词完全是表音的不表意,比如便宜,是pianyi,这两个字是不表意的。有一些四川话的词相反,会有非常强的方言特点。与此同时,又能够让其他人看懂。我看爱用四川话里面四个字的话,比如我们形容一个场景非常吵,我们说“鸡叫鹅叫”。写出来这四个字是大家能够领会到的。 还有一些非常雅的词,比如说一个地方很安静,叫做“清风雅静”。写出来的这四个字也有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在唐宝珍里面有一句很典型的四川话,讲这个离了婚的漂亮女人在小镇上走过,大家都盯着她看,有这么一句话,“她咕嘟嘟的鞋根子嗒嗒地踩着大家的心尖尖”。会有这样一些音律性的,或者是这个地区的人讲话的体会,是一种轻快的音律性的,甚至是自带幽默的语言。我是希望把这个地方传达出来,在让更多的人理解的前提下。 |家乡滋养写作|
 作家七堇年 摄影/杨公振 七堇年:这个充分解释了我私下里一直想跟她探讨的疑惑,其实她是经过了甄别,而不是把方言本身拿出来,就像她说的关起门来说话。比如四川人问你什么,一定会说啥子。这样写你们也能领会到,但她用方言写作的技巧上,是非常用心的。类似的作家有很多。 颜歌的作品,从《我们家》开始,应该是你近期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坚持的方向吧? 颜歌:是的。 七堇年:接着我就想提到一个跟颜歌一起探讨的,就是平乐镇。虽然这个名字是虚构的,但它具有很实体的背景,也是你成长的家乡,郫县这个镇。你在家乡的少年时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滋养了你的写作。 颜歌:其实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当时这个书出来的时候,我跟我的编辑都在想这个书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最后如果非得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的话,就是怀旧、怀乡。我觉得这是作为作家的一个点。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作家,有的作家是异想天开的,像卡尔德诺。有的作家是博大精深的,像伯尔克斯。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像我这样的人,我是非常怀旧的人。 我不知道小七有没有听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叙事学教授讲过一句话“一切的叙事都发生在行为之后”。他其实讲的是很白话的,你把一个东西描述下来的时候,成为叙事的时候,这个事情肯定是发生过的,这是很理科的分析法。这句话让我很伤感。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小说家,我是一个叙事者。我做的所有事情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写古今、过去的事情。我是一个永远向后看的人。 所谓的平乐镇,平乐镇可以说是我的家乡,也可以是很多很多的镇。可能在座的朋友比我年轻一点,我姑且说我的同龄人,我认为是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有的城乡接合部的成长经历,在8、90年代的时候。我写的是这样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普遍的,我觉得是令人伤感的。 七堇年:曾经我跟一个比我们更小一点的90后的朋友探讨过,关于家乡,问他们有没有根的感觉。现在城市发展之后,大家在城市都是处于大同小异的生活状态,住在小区里。我们80后这一代还依然会有邻居家访,家乡的记忆一直深深地留在那儿。我知道颜歌你长大之后,她除了在成都,要么就是在家乡待着,要么就是走得很远,在杜克大学交流的时候,去了一年。她有很多国际友人朋友,包括她的阅读兴趣也是非常国际化的,能否谈谈这些经历,跟你的家乡背景写作的关系。 |离家越远,写得越好|
 作家颜歌 摄影/杨公振 颜歌: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是什么背景。我是一个宅女,我生在成都郫县,在川大念书,从本科、硕士一直念到博士。我没有真的离开过家。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离开家的时候就是我去杜克念书的时候。我在杜克的时候,是我写《我们家》的时候。换句话说,我是在离开我的家乡非常远的环境里,开始想到要写我的家乡,而且是用一种还蛮奇怪的方式,写了一个中年人的生活,或者可以说是不美的家乡。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词——“怀旧”。我非常喜欢这个词,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姑且叫做怀乡情怀。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很难找到一个中文把这个词翻译得很清楚。因为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对你的家乡的怀念,就是你之前来的地方,在地理上的怀念。 第二件是在时间轴上对过去的怀念。所以它是对故土的怀念。我在杜克的时候,经常想到这个词。我也是怀着这样的情绪,更多地想写我的家乡,写我故乡的事情。当你把它放在一个怀乡的情绪上的时候。当时我的情况是你不在时间上回不去,在地理上也回不去,这是我感情的喷发点。所以我就有一个理性,我觉得我好像跑到离家越远的地方,就会写得越好。 其实小七还有一点是她不知道的,我开始写平乐镇,就是所谓这个小镇的第一本书是《五月女王》,是在福州写的。《我们家》是在杜克写的。我当时有一个迷信,可能我要搬到火星上去才能写下一本。我发现很奇妙的是当你跟一个东西隔绝开的时候,比如我在美国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没有中国人,只是你写的东西是别人没有兴趣的,它是非常小的东西,是四川的小镇上发生的事情。我发现我第一次做的事情变成了修行,变成了跟我周围的人都毫无关系的一件事情,在我人生中是第一次。也是非常不幸的,或者幸运的,我跟小七挺像,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表作品,开始写作。在某个程度来说,你的写作是在进步,你是在写作,但你的写作是一直被观看的。 当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每天在教室里面写,我在图书馆里面写,没有人在乎我在干什么。就算是有一个人在乎我在干什么,他坐下来,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我写的东西是什么。对生活在我周围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不重要的,是陌生的,是无意义的。我觉得是第一次在完全没有人观看我的情况下写的东西。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变成更坚强的人,更坚定的作家。 我觉得走远一点写是有好处的。 七堇年:我其实挺有这种感觉的。好像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一个附和。我说的就是她的那个意思,就是这种感觉。 回到这本书当中,因为她的家乡特色和方言特色是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再多讨论一点。这本书的序,我是很早以前就读过的,包括其中的《三一茶会》,也是我之前在《收获》上读过的。一些电影把很多人的家乡记忆美化之后,或者是经过修饰的记忆,很美好,完全把它美化过的。我老家是庐州的,我每次回家都觉得它的脏乱、落后,既新,又旧。我既熟悉,又忍不了它。离开家这些时候,我在国外生活过,现在也在北京这些城市。她在序当中写的那个点,回去之后看到的中巴车,依然生活在那儿的平民们,他们现实中的状态,跟颜歌自己提到的你想离文明更进一步,一直读博,读到现在。这种城乡接合部,跟你本人之间是否有矛盾?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有点恶趣味|
 作家七堇年 摄影/杨公振 颜歌:我发现我是有一种恶趣味的人。我是不相信真善美的。我觉得真善美这三个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要么真,要么美,那善是什么?我其实是有一点困惑的。我是有一点恶趣味的人。 小七讲的,我非常有同感。广义上来讲,我们算是老乡。你回到你的故乡的时候,包括现在我每次回到郫县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很触动你的东西。因为我是一直在学校里的人,这些东西跟我自己的生活轨道是接不上的。小时候我会特别嫌弃它们。 想起来挺逗的,我特别小的时候出书,那个时候写的都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叫做玄幻,那个时候就是“你到底在写什么?”写了非常不着边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每天在郫县两点一线,从学校到家,我恨死了这个地方。我要写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个地方,我要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去那儿休息一下。我要好好念书,或者是要有出息。因为我要离开这儿,这儿太让我受不了了,乱七八糟的。我小时候跟人家讲四川话都觉得很耻辱。 很逗的是到了现在。其实我也不住在家乡,我居然变成了不定地怀念它的人。这句话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意义。就算是到现在,我一直还认为我高中时候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老是会回想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挺讽刺的事情。叫什么?小时候不要随便许愿,许下的愿会反过来弄你。小时候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我不停地回到这个地方。 当我真的见过了很多大家所谓的好的进步的文明的先进的东西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小镇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曾经被我们认为的丑陋的肮脏的混乱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坏的。就像我刚才说真善美这三个概念不是能同时存在的。美好和丑陋是一个二元对立,但并不是说美好就是正面的,丑陋就是负面的。因此,当我回来看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心情。这些东西如果仅仅在文学上,它是极其丰富的。当时我在写序的时候,我说我是充满了恶趣味的在垃圾堆里面翻找我要写的故事和人物。这些东西是有趣的,有趣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这是最重要的,它是真的。你是要真,还是需要美?我个人觉得这两件事情不是兼得的。在我的世界里,我选择的是尽量地接近真东西。 |四川人的08年分界线| 七堇年:大家可能都对2008年的汶川地震有印象。我现在想起来挺遗憾。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没有在家乡。现在在四川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如果说起某件事情,会以这个地震为纪年。比如我跟他是地震后离婚的,或者这个房子是地震前买的,这个地震变成公元后多少、公元前多少。我自己没有亲历这件事。我从这个现象中发现这样一个事件在这个地区的人文生活中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是出版社列在里面的,我在作品当中没有读到关于这个部分的痕迹。在2008年地震之后,感觉自己可能很久都没法对目前的现实发出声音。所以写过去的事情。刚刚你提到的,你并不相信这些。在这个作品中,如果用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词来概括,你到底挖掘的是什么? 颜歌:我觉得很难概括。如果非让我概括的话,我觉得是复杂。如果我自己能用一个东西来概括我自己的小说,我就不要写这个小说了,我写一个微博好了。 我的《我们家》的故事,写的是2007年。我在这个小说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时间,比如1995年、1998。当然,迄今为止我写的所有的故事没有一个是2008后的。这是因为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写。这对我是一个课题。不只是因为地震,是因为现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当下,如果我们现在说2015年面对的这个庞杂的大数据般的现实,我们每天生活的,我们接触信息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是戏剧性的。我觉得是很难让我去理解的。我觉得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希望表达现实。但是,这个现实还没有让我找到表达它的方法。在我的作品里,我用2008年作为我作品的一个标记,我现在写的都是前地震。就像你说的,在那个以后,因为我写的就是这一块地方,写小说的重点不在于说编故事,而在于说你要把细节都凿实。如果有一个地方走火了,大家就觉得你在编故事,你就完蛋了。在这以后的很多事情,我还没有能够非常好地把它吸收进来。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如果我要写的话,我就没有底气。所以我不写2008年以后。 七堇年:她说了这番话,我要说同意,又要说不同意。 之前我跟一个前辈老师讨论,他说现在很难看到真正好的小说家。大家带有很多的情绪,比如用第一人称,像我这样的,就是典型的在铺陈自己的情绪。其实我完全清楚。我就问他你看过颜歌的小说吗?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尤其在这本书当中,我真的是要说颜歌是以小说家的要求和技巧原则,真的是在写小说。你能从这些文字当中感受到她的沉静和克制,和那种展现。她并没有那么多的判断,但她的展现,你不要看着这些文字是很克制、很平静地用四川话来讲,人生无意义的流淌之中所能展现的探索都呈现在其中了。 我想给大家读一段,她的后记的开头逗得我哈哈大笑。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写了五个故事,从2008年到2015年,我也就过完了自己的所有20几岁,松了一口气,《白马》是写的最早的。 |对不可靠叙事者喜爱的一次纵容| 七堇年:看完后记,你至少会对她的小说有一些理解。我在所有文章当中,最喜欢的就是《白马》。我一向不擅长概括。你来概括《白马》这篇写的是什么故事。 颜歌:随便问作者让她说自己的问题,这是违法的。其实我也是可以回答,但我的答案非常为难。我是作者,从作者的角度来说,《白马》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自己,对于不可靠叙事者喜爱的一次纵容。 七堇年:听懂了吗? 颜歌:《白马》里面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什么是不可靠的叙事者?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靠不住的。我写《白马》的时候,就是想写一个非常轻松的东西。我写《白马》的时候刚刚地震完,2008年6月份的时候。为什么有之前那段跟诗人在一起。那个时候成都人开始是躲地震,后来在外面玩儿不回家,全成都的人都在外面喝酒、打麻将,赶大家回去,都没有人回去。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成都的文艺社群最紧密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天天都在外面,才有了这一段。 在那个时候,我想写这个故事。《白马》里面写的大概是1993年的两个姐妹之间的故事。虽然是一个好笑的故事,但我是挺伤感的。那个时候在街上走,每天就是拉警报,过会儿就说要去超市,每次去都要把所有东西买回来。你知道这个情况会过去,但在当下你会有一种非常惊慌的心情。我作为一个书呆子,就在这样的现实里面,选择了写一个非常美好的可能再也不会有的过去。 《白马》里面有一个“我”,有一个姐姐。那个姐姐的原型是我的一个表姐或者是堂姐,我一直搞不清楚,妈妈的姐姐的女儿。她是都江堰人。我当时为什么想写这个故事?都江堰当时是地震的灾区,她是在都江堰,我是在郫县,我们很近。我的每一个寒暑假都是跟她一起渡过的,因为她只大我1岁,我们相当于最近的姐妹。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我在都江堰的姐姐,所以就写了这个故事。 七堇年:谈论这个小说的时候,相信大家如果看过之后,会对她谈论的更有感觉。可以这样说。比如我想问的,当你们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想象白马这个元素在小说当中扮演的是什么东西?我很好奇。 颜歌:《白马》这个小说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个英文版本。出英文可以出一个小小的短长篇那样的小故事。我10月份的时候也去英国做了一些活动。所有的采访全部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人家那个问题问的很逗,是他们所有人都觉得因为是马年。大家都问我说“因为今年是马年吗?”这个问题你问,我要回答你,就必须更真诚一点,就不能用随便糊弄外国人的做法。 白马这个意象,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随机的形象。它可以是白马,白象、白鸟都可以。我是随机选择的形象,我让它在故事里反复出现。这个反复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给读者递的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时不时的就有白马。于是,这个时候读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叙事者在故事里面的人,她是一个精神有障碍的小孩。所以白马在一定意义上是叙事学的教育。当一个不能以现实主义的常理解释的元素出现的时候,请大家不要立刻认为它是魔幻现实。作者和叙事者之间是有差别的。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写的小说,我每次都在里面干一个特别特别书呆子的事情。每次说出来,我都觉得很丢人。 |我是一个书呆子|
 现场照片 摄影/杨明 七堇年:你已经反复强调了十几遍书呆子,有这么样的书呆子吗?咱们心里都有一个书呆子的形象。我看最后一排的男生一直笑。 颜歌:我真的是一个书呆子,为的证明我是一个书呆子,我两只眼睛,每只眼睛都有1千度以上的近视。 七堇年:你们不要笑,其实她看不清楚你们。 在这本书当中,总结性的谈一下我看这本书的感受。我读得书很少,不敢随便说。但是,我觉得一般作品中都有作者的判断和情绪。我最喜欢的是颜歌在这本书当中,她的那种自然和特质,她不带有那么多的判断,她的呈现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颜歌的作品现在陆续被翻译为很多国家的文字,也有很多翻译家在跟她沟通,就觉得很头疼,尤其是《我们家》和这本《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翻译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她的方言特色,包括她的作品中,比如像《三一茶会》描述了一群老年人每次聚会,都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得涩得涩,小范围里面自得其乐的感觉。我确实可以想象对翻译有很大的挑战性和难度。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