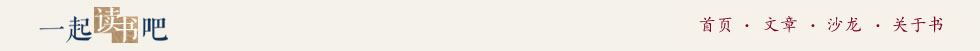童年琐事注定一生
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 生我时,住在天津的爷爷奶奶来北京,下火车后从车站打了个电话问生了吗?是男孩女孩?听说是女孩,马上买了回天津的票。 小时候儿,我特别喜欢姥爷的书房,姥爷每天早起要“站桩”,往那儿一站,张着嘴,半天不动!这时孩子们一点声儿不许出。十一点半以后可以进他的书房看书,有中国的外国的,小孩儿的大人的书。他有几位美国的好朋友,常送他东西,也送他外国儿童图书,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书,急着翻页,免不了撕书,听到撕书的声音,他坐的皮转椅“嗖”的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我就得过去自己说打几下儿。我小时候儿特笨,别人使眼色也没有用。我姐姐撕了书,总是说:“打两下儿吧!保证没有下次!”我总是说十下儿。我母亲说:“你下次别说十下儿就说三下儿。”可我还是老说十下儿,不知是吓糊涂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我受惩罚还因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饭说话,吃饭吧唧嘴。小孩儿有小圆饭桌,年纪小的先动筷子要受惩罚,饭再好吃,一边儿罚站吧。吃完饭扫地,好多个孙子孙女儿,轮流扫地,扫不干净要受罚。 从父母和家人的只言片语里我了解了一点点他们的青年时代—母亲怀我的时候,仅二十几岁,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父亲在清华时,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教书。划成右派后,因为他很能干,就以“劳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去。实际上他是设计师,因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劳工待遇。母亲便作为父亲的替罪羊,被下放到东北长春吉林画报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国内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大家一再嘱咐你爸‘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也不要发表意见!你爸守口如瓶,最风火的时期躲过了,没被划成右派。运动结束时,上级嫌清华大学右派名额不够指标。瞧!就发了一次言也给打成‘后补右派’了,害得你妈被下放东北,北京正在大兴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发挥才能。” 母亲说:“可你爸还真心为了祖国更好。” 母亲被下放,我三岁,去东北还太小,母亲就带上了五岁的姐姐。母亲本想把我托付给姥姥,但姥姥家已经有一个孙子,一家之主是姥爷,收养孙子比收养外孙女顺理成章,在姥爷眼里,小女儿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亲。父母就把我送进离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一家四口从此拆到东西南北。 那几年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她不大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别老问我这些越说越难受的事儿,好不好!” 那时是饥荒的时候,她谈过一点点饥荒的事儿,“没有东西吃,大家都浮肿,全装病去医务室拿大药丸子充饥。那还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孙老庄时……山坡上的树皮被吃光,冬天,因为所有的树都扒光了,树冻死了,来年连吃树叶的可能都没有了。” 我姐姐在吉林画报社幼儿园。夜里她把玻璃窗打破,穿着睡衣,沿着铁路走,冻得不成人样儿被大兵拾回来。她说梦见姥姥,想回姥姥家。与此同时,幼儿园还出了另一件事儿,一位阿姨惩罚一个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儿,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后来给忘了。一周后孩子的父母来接,她才想起来,到幼儿园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儿浑身是血,头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亲吓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特别不好。那年我三岁半,还不太会料理自己的起居。冬天阿姨惩罚我站在外面,“什么时候你学会自己穿鞋,什么时候我才让你进来!资产阶级也要自力更生,懂吗?”我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我两只脚冻得肿大,穿不进棉鞋,手也红肿得像五根胡萝卜,烂了。 星期六没有晚饭,孩子们在走廊里,面对面坐在矮长凳儿上,等着家长来接。我眼巴巴地盼呀,盼着父亲早点来接我。父亲每天在工地劳动以后,还要去学校给学生上晚自习,所以他星期六来接我常常迟到。一般五六点钟的时候,孩子们都回家了。有一次都晚上十点了,我还坐在长凳儿上等他,我想去厕所。刚进厕所,就听到阿姨大喊:“李爽,你爸来了!”平时我很恨这个阿姨,她常常罚我的站,我只记得她姓雷。我连屁股也没擦,俩手提着裤子冲出厕所,走廊显得如此漫长,我拼命地跑跑跑……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使劲儿抱着父亲脖子不放,听着雷阿姨像往常一样数落爸爸来晚了。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勇敢些,大骂她!可父亲从不回嘴,还笑着赔礼道歉。 我依然记得雷阿姨的样儿:中等个儿,不胖,短头发很黑很齐,大眼睛,面唇边一颗带毛的痣。她把我推到墙根儿,弯下腰脸离我很近,用指头一下又一下戳我的额头,说我,我学会了“听不见”,居然可以数出她的黑痣上有四根毛,一根长三根短。以后在街上甚至在生活中,遇到长得像雷阿姨的女人我都反感。 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会不自觉地加倍宠爱我的孩子,仿佛把他们当作某种替身,看见他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我会想:“如果我当年能有这些爱该多好呀。”真的,我不希望任何人在童年时代受到任何心理上的伤虐。那种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幼年的心理阴影是拖累,使人混淆在心理时光中不能自信,童年的负面记忆是很难疗愈的,甚至可以污染所有未来的美好时光。 只要有时间父亲都会给我讲故事,听《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伤心地为小女孩儿哭,听《皇帝的新衣》我笑破肚子,听《拇指姑娘》我浮想联翩,听《西游记》我到处练翻跟头,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吓得我往被垛子里钻,做了一夜的噩梦。 星期天父亲会偶尔带我到外面吃饭,这是幸福的时刻。 有一次我们俩吃完晚饭,顺着街往家走。父亲忽然说:“哎呀!我把书包忘餐厅了,你在这儿别动!等着,我跑回去拿。你和我一起跑太慢,书包会丢了。”他迈开大步往回跑。等他的时候儿我扬头看天,几个星星串在一起很像一把大勺子。父亲拿了书包回来,我问他,他就给我讲那是北斗七星,最亮的那颗是北极星。 我至今常常在夏夜看这个星座,每回都好像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一次,星期天,父亲带我出去玩儿,晚上回来,正赶上姥爷姥姥要去看《白蛇传》。我父亲说孩子睡着了,老头儿就让他进了院儿,之后就走了,可实际上院儿里的门都锁着,进不了屋儿。当时已深秋,父亲说他等到很晚了,第二天还得去工地,孩子总冻着也不行,就从厨房往客厅送饭的窗口爬了进去。把我放在小床上,又钻出来在外面坐着等。 老头儿回来大怒,“我们是什么人家!还有会钻窗户的!” 我父亲虽然骨子里非常中国,却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他喜欢听唱片,老外的唱片他都有,还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我们最大的享受是听他拉《蓝色多瑙河》。到现在每次我走过巴黎街头,一听到卖艺人拉手风琴,就想起父亲,心也马上即收又放,荡漾着无名的甜,但是那个甜中也有许多酸涩。 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带着右派的帽子调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母亲一九六一年从东北调回,也进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英文。一家人团聚了。 我母亲年轻时喜欢打扮,这时又从箱子里翻出来几件好衣服穿上。这是一段难忘的幸福日子—我们姐儿俩,快乐地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父亲,在颐和园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书料 一起读书吧601期,今天观点君跟你分享来自李爽的《爽:七十年代私人札记》,本文由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李爽的名字会让现今许多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人感到陌生,但李爽却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等一起,是70年代末风潮迭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先锋之一。 北岛说,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从少女青春期迷惘的摸索,到加入破冰之旅的“星星画会”,并导致与法国外交官之恋的坎坷经历。李爽的自传《爽》,其名印证了她一生中的性格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