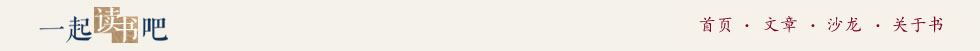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
 8月2日下午,北京言几又书店二层笑声不断,一大部分功劳要给来主持读书会的史航,他在微博上刚刚跟一波粉丝“吵完架”,而且还赢了。这次读书会的主人公是“县城青年”绿妖,带着她的短篇小说集《少女哪吒》来跟读者见面。有些人没看过书,但看过李霄峰导演改编的《少女哪吒》的电影。是的,李霄峰导演也来了。 绿妖被史航一脸坏笑地爆出了写在《少女哪吒》序言里的真实姓名“王海燕”,低头掩面,她觉得这名字太恶俗了。绿妖说,“我感觉我没有办法把(捂着脸的)手拿开。”也是在这个玩笑后,现场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史航说,“现在我们放松多了。”
  绿妖:我回想少年时代,是为下一段人生寻找力量
 《少女哪吒》里大部分文章写于2012年到2015年,那个时候我30多岁了。作为一个专业写作的人,我好像刚刚进入一个专业写作阶段,之前一直在上班,写作也是野路子。 有段时间,我觉得写作者写不出来作品是很大的耻辱。写不出来的时候,觉得生命意义被否定了。然后就这样想啊想,于是我不停地回想起我的少年时代的一些认识的人,我的一些玩伴、同学、朋友。 提倡“人智学”的华德福教育创始人鲁道夫·施泰纳说过,小孩子可以多给他阅读一些东西,不要怕他不懂。这些东西当时他会不理解,但是等到他30多岁其他领域成熟会带来这一部分的理解。那个时候苏醒的东西,是人生继续下去的力量。我突然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回到少年时代去想一些事情,其实是在寻找下一段人生继续前行的力量。 最开始我回想少年阶段,其实碰到的是贫瘠。 我的少年并没有遇到让我特别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权威。我转了很多次学,最后我的中学校长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专制主义者,有的男生不听话,他就把调皮男生关到地下室关了八个小时,这是非常残暴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非常反抗这些东西,包括家庭、教育,学校。 在走过最初的回忆里的贫瘠地段后,我就想少年时光难道就不能为我提供什么东西,让我继续走下去了吗?然后不知不觉地想到少年时候的其他东西,就是自然界的美。 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条河,然后那个河边有河堤。我们小时候的河堤是一个果园,春天时候苹果树开花,梨树也开花,杏树也开花,对小孩是一个乐园,我们一放学就会奔向那个乐园。这些东西慢慢进入我的记忆,我才觉得我的少年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另外一种力量存在。 《少女哪吒》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变成这本书大部分的故事。
 今天来很多人可能都还是少年,我觉得有一个阶段是20多岁即将进入30岁的时候,27、28、29岁的时候,身体明显有种磨损感。 之前,我连着熬五天都没问题,第二天洗一个脸就去上班。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熬一夜可能要在床上躺一天的时候,就觉得身体很多地方不配合了。尽管你的意志还很敏锐、很旺盛,想要去做更多事情,但是身体这里那里开始疼痛了,你开始频繁跑医院了。我不知道那是社会对女性身份的一个定义,你到30岁就什么都不是了、让我开始有恐慌感了呢?还是说生理到那个阶段自然就会提醒你有磨损感。 但是好在过了那个坎,真正到了30多岁我就觉得又很释然了,就是自由了。我突然又感觉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天地,那是一种属于小孩子的敏锐感。 如果你不给自己太多束缚,那种敏锐感会持续,尤其在写作上。写完小说,你刚刚写完一篇小说的那几天,是特别敏锐的时候,走在街上看到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这个人脸上写着他的剧情前传。每个人都是本移动的短篇小说,那种感觉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然后对世界分外敏锐,就觉得颜色特别鲜艳,但是要经常在创作状态里才有这种敏锐感,如果你掉出来,不经常写,可能就会淡一点。
 我看完电影《少女哪吒》之后写了两条微博,我说,“这是一首诗,关于少女灵魂的纯洁诗歌,带着炽热而孤独的灵魂,我很喜欢”。刚刚提到一句是,“你不要乱扔东西,这是我跟李小路的地盘,我带你来我还没有跟她说”,我特别喜欢这一句。 我把它用在最后一篇,李小路长大以后又回到保成,跟刑事案件卷入的时候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孩子气的东西,孩子会觉得跟自然是长在一起的,他会觉得童年的乐园就是乌托邦,别的他是看不到的,我只看到我的好伙伴,我们在这里待着,头顶着头在说话,不停地说话,小女孩儿有很多话的。 等到你再长大成人之后,好像觉得这个河堤也破破烂烂的,树也没有那么高,小小矮矮的,或者树都坎了,河堤以前的果园变成水泥地,觉得那个世界没有那么美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望出去,曾经是孩子的眼睛可以把世界点石成金,到处焕发光芒。 很多成人重游故地,发现童年很多东西失去光芒,写作者唯一的便利就是可以用写作留住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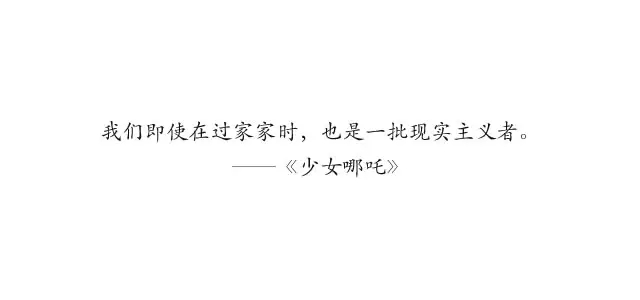 史航:只要没在青春夭折,我们必将在中年会师,更关心对方
 △史航
看到拘束,看到敏锐。 刚才在想说到磨损感的时候,我想起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认识他们,在西祠胡同。那时候我们是网友,现在仍然是网友。 2001、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饭局基本上三天一聚,那时候最嚣张是六局连放。周六吃饭,然后喝酒,然后去唱歌,然后天亮去喝酒,喝永和豆浆,然后晚上再吃饭,然后再看电影,就跟铁人三项一样。现在说起来感觉这是一个纪念性话题了。 你刚才说的磨损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感受很多。我们都见过别人的醉态,我们见过彼此的醉态。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说,“我们一起听过午夜的钟声。”我们午夜该回家的时候我们都又不回家了,过了12点发现你也不是公主,你就是灰姑娘,他也不是马车,他就是一个南瓜。 人到中年,互相把对方当一本书的时候,开始打开读,发现对方真的也有一个书签。有时候是夹一张粮票,有时候是一张作废的电影票,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人心里藏着东西,而且我们会双手打开,双手把门合上,不管中间看到什么,有的人写出来,有的人导出来,有的人可能只是偶尔说起。这些东西只要没有在青春夭折,就会在中年会师,我们会更关心对方,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总得有一个人,有一封信,证明你不是从石头崖上蹦出来的。” 这不是说给别人看你的身份证或者是家庭履历,而是说我有过朋友、有过敌人、有过后来和好的朋友,有没有写完或者没有寄出的信,这些证明我有过的青春。我从青春这边到那边来,对每一个人是一个提醒,如果你忘了所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不是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学历——而是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生长和成长的经历。
 所以我们依赖于我们要记的这些人。我是长春人,我发现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我名字记不全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记忆力特别好,炫耀这个。我们高中同学71个人,后来我发现90年代末有一次聚会,在长春有一个咖啡馆,我炫耀性地写名字,我发现我只写出51个人,我有20个人名字记不住了,当时我特别着急,但是现在我连51个都记不全了。我记不出来对我不是损失,对别人也不是损失,人家可能都不记得我这个人了。我写再一个Word里面过后不一定看,但是写在本上也不一定看,我也不一定写在墙上,太变态了。怎么办呢?我说我得记住他们的方式,我写微博置顶也没有用,这个东西写不了那么多。但是我写一个小说集,比如说我认识我们班生活委员王海燕,体育委员李霄峰。我把不相干的,不认识的长春人写出来。然后起一个动物名字来记住,最后我会出书。但是简单目的就是我想记住这些名字。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香港九龙有一个叫曾灶财,他喜欢到处写名字。后来大家都赶着抓他,把墙刷掉,后来发现奇怪的字,大家有印象,不刷了,成了香港财富,开始用他的名字设计包,设计衣服,最后他死去了。香港拍过一个电影叫《九龙皇帝》,就因为他每次落款就是香港九龙皇帝曾灶财。
有时候电影就是这样,虚构文学就是这样,一边虚构一边回忆,因为让虚构回忆更安全,更立得住。
绿妖她去过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的小学,当了一段时间老师,她也还能上网,刷微博,我们可以微信联系。我说这件事不是表扬好人好事,我想说的是,一个逃过县城的少年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县城,一个走出教室的人可以走入另外一个教室,她跟一般的文艺青年不一样。法国一个作家说,他应该是一个异乡人,带着你不同的口音来到这里。我们成长期都应该遇到这样的老师,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少女哪吒”,她不是在闹一片海,她可能是在滋润一个山区。这是一个编外故事,告诉文艺青年有很多种故事,绝不只是叹息,这是最重要的。
 李霄峰:长大后的生活,与小时候的愿望总是南辕北辙
 我找绿妖要《少女哪吒》小说看,第一感觉是震撼。因为她是用一种类似于书信体的感觉写下来的。人一用书信,用第一人称,你很容易感觉到这是两个心灵的世界。你能够感觉到这是两颗心脏在跳动。然后我看的时候就特别震惊,我在想我中学那些女同学搞了半天都在想这些事。
真的,我特别震惊。
因为原来我后边坐过两个女孩儿,她们俩上课天天传纸条,一个班长,一个学习委员,也很“恐怖”。我以为我跟她们关系很好,因为我们上课,我也经常给他们传纸条,有的时候聊聊班上男孩儿、女孩儿八卦。我看完绿妖的小说才发现,这些女孩子我一个都不了解。她们十几岁的时候心理那么丰富,那么敏感,完全自成一个世界。这是男生没有的,男生相比之下就太“愚蠢”了。
她的小说不能看一遍,看她的小说不是看情节的、不是看故事的,是看人、看内在的东西,那个劲是慢慢渗透出来的。到我已经决定要拍她东西的时候,要准备材料,那天是2013年端午节。我要从合肥回北京,临上飞机之前,我要再把小说看一遍。第一个大段落就是王晓冰写的作文,初中时候她得奖的作文,最后一句话是,她说“我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我希望能够跟它永不分离”,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但是我不是第一次看这小说,我看了好多遍了。我一下子都没有反映过来自己在流眼泪。有时候人哭的时候,是本能先出来了,理智还没有跟上。过了几秒钟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哭?后来我一想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女孩儿她做不到,我自己也做不到。后来发现,长大之后的生活跟你小时候愿望是南辕北辙,你希望你向南方走,但是长大以后一定往北方走。
我在改编她小说两个多月里面,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因为我是男的,不是女孩儿,但是我又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女的,我要跟这些人物相处。我每天看这个小说,改编作品过程中,我就发现第三层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少女哪吒》里的王晓冰,那么特别,那么浪漫的一个人,而这样的人在我的生活里面已经绝迹了,在真实生活里面已经没有了。
他们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我们还是在银幕上、在文艺作品上里,能找到这种特别的影子,这是我最后发现的东西。





 摄影/杨公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