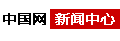林湄:十年磨一剑,文学即人学

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主编):尊敬的各位导师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中国女性文化论坛,参加“荷兰华裔作家长篇新作《天外》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我们和新世界出版社联合主办。外面是寒冷的冬天,会议室里暖意熔融,我们相聚在这里谈论文学,是非常幸运的事。
首先介绍一下林湄老师,林湄老师是海外女作家,可能大家不像对国内女作家那么熟悉,林湄老师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外》,是《天望》的姊妹篇。她是十年磨一剑,她到欧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漂泊》是1995年出版,《天望》是2004年出版,再十年磨一剑,新长篇《天外》2014年出版11月才出版问世。
她是世界华文文坛上非常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我说明两点,第一点,她富有大悲悯的宗教境界,追求普世价值的经典情怀,是一位严肃的纯文学作家。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作家能够坚守创作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2004年出版《天望》一出版,就受到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家的关注,赢得广泛赞誉,我们曾做了题为“洞察世间万象,寻找人类文化与灵魂救赎之策”的专题论坛。第二点,她的作品不是那种特别宏大的架构,是画卷式的网状结构叙事。她能够把诗歌、散文、学术、哲学、宗教等都融入她的小说里,在阅读她的小说的时候,牵动你的可能不是情节,而是她的思想和精神流向。所以,评论家们常说林湄老师不仅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思想者。这在海外华文作家里是不多见的。这次她特意为新作《天外》出版而回国,今天我们对她的新作《天外》进行研讨,大家一起鼓掌,祝贺她的新作出版。下面首先让林湄老师来谈一谈,她从《天望》到《天外》的创作感受,大家欢迎!
林湄:(荷兰华裔作家欧华文学会主席)
谢谢各位专家、老师的到来,在纯文学不景气的当下,有机会与祖国同行者座谈文学,实在难得,我再次对各位深表谢意。
我祖籍福建福清市,出生在丝绸之路的泉州,华侨世家,70年代移居香港,90年代移居欧洲,现在是荷兰籍,一生经历了社会主义、殖民地香港及资本主义社会,虽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植于我灵魂深处的根本东西还是中国文化。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颇有文学天赋,但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主要还是靠勤奋和契而不舍的毅力。在香港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时候,除了工作外业余时间写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题材大部分跟我个人的经历与周遭人的命运有关系。
我是到欧洲后才对“文学即人学”的感悟,确信了无论欧洲人还是东方人均离不开人的共性和个性,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欧洲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21世纪信息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促使我想起歌德1827年1月对爱克曼论及的“总体文学”,即对“世界文学”的再思。
“世界文学”不分民族、身份和国界,触及的题材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人的彷徨,迷茫,生存处境以及对财色生死问题的探索,居住地球村里的人,任何荣辱福祸均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还有诸多形而上的问题困扰着人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每天忙忙碌碌又为了什么,精神和物质、灵与体、有限与无限等等问题引发我思考的兴趣。
1995年6月,在荷兰召开了我个人的作品研讨会,有50多位学者专家参会,80多岁的《红楼梦》法语翻译家李治华说“林湄的小说题材多是关注社会的重要问题”,比利时汉学家魏查理院士表示“林湄的小说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均能接受”,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教授戴翊上交万多字评论“女性的命运与辉煌”,等等论文,以及会后有20多家的传媒报道,但我觉得文学艺术是无穷无尽的,与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还差得远,决意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此后,我拒绝一切诱惑,甘于清寂、淡泊名利,没有办法去改变社会现实,只好将思考融入我爱好的文学创作里,用十年时间完成5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望》,男主角是有救赎思想的人,他以简单对付世界的复杂,世人觉得他傻,他却觉得世人傻,认为众人活得又累又愚昧,个个均在追求财色和物质东西-------
《天望》写完了,出版后获中外专家好评,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生活在继续,社会在改变,科技在发展,生命短暂,文学却没有完结------更重要的是,其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影响了海外华人。华人带着完美主义的理想,从东方到西方,不料西方渐渐没落,东方却在崛起,漂泊者自然对离散、移居、身份等词语有着更多的解读和理解,我不由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意,一生劳苦愁烦却只得一口饭吃。
可见,现代高科技与经济发展并没有带给人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相反,其带来的付作用却隐约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灵魂力度,使其潜移默化的异化,或怪诞、或萎缩、或不知所措-----
藉着对社会人生的忧患和拥有的创作激情,我再次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天望》的姐妹篇《天外》。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思想相当复杂,思考多于书写,每一章,每一个人物均寄托了对社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于是,以第三空间的视角叙写众生相,集平凡人的生活、际遇和命运表达人生的劳苦与愁烦及无奈焦虑的存在。书里的人物均是现实生活中群体的代表,如一个欲望的结束就是世人另一欲望的开始,永远不会满足,中国人如是,西方人也是如是。
物欲的充塞,使人的灵魂都丢失了,作为作家就有了负担,只是无法改变现实,幸好依然热爱文学,加之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天真无知,常常做蠢事,因而,写作是我承受命运的最佳状况,也是我祈祷似的生存方式。
有人说,你的小说不入流,难读,难懂,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有距离,给阅读和审美习惯带来难度与费解。确实,近20多年来,我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不尽与传统文学观不同,也与自己1995年之前的创作不一样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我离开祖国已41年,“根”既移植,吸收的养份就有所变化,结出的果子自然也会不同。为什么要一样呢?事实证明,即使在同一社会环境下成长、同校同系的毕业生,也会出现不同的求索精神与出路。何况,古今中外,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观,也无永远绝对的“正确”,或出于我智、识的求索,或与我生存环境有关,或因我较具前缘性意识,所以,行走在文学艺术的求知路上,喜欢独立特行,希望在探索中创作独具一格的作品,将传统小说强调故事、情节、重悬念、冲突、高潮等创作法与西方的慢节奏、细观察、重视人内在意识和心理变化的特征相融或掺合,在叙述命运和各人性格里反映社会人生,让艺术结构和形式更好地表达人类生命底本质,当然,更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思,有所启迪,不是看完就完事的感觉。
我崇善经典,有些“离经叛道”是求索。即杨老师所说,形而上思考,形而下观察,通过几个家庭各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各式各样的麻烦,反映现代人的心灵被物化、财化、色化等扭曲了,其心态与作为就是社会的写照,让人思索生存的艰难、无奈与感叹!
以天上的视角,对于红尘滚滚中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充满忧患和悲悯,两位杨老师已看出老祖祖的符号是救赎,人类究竟往何去?等等------
总之,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享受快乐和满足,至于后果如何,那不是作家的事了。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时代同龄人聪明得多,要相信和尊重他们的才智和选择,因而,无论当下纯文学是如何地举步艰辛,我依然会痴痴地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