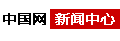女性文学经典化与跨界书写
主持人:陆卓宁 林丹娅
张抗抗:女性书写的深化与拓展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探究女性文学的经典化问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研究基地,对女性文学创作研究提出了一个高的标准,呼唤经典、催生经典。 “经典化”为我们女性写作设置了一个目标,当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写作的人,不一定很在意。比如我自己,并没有书写经典的野心。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经典?那是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是尽可能把作品写好。卡尔维诺说过,“经典就是那些你正在阅读并且会再次重读的书”。这应该是关于经典的其中一个定义,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鉴定。我只想谈三个方面的体会,就是女性写作如何自觉、拓展和深化的问题。

张抗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名誉主任
第一,是女性写作意识的自觉。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写《北极光》《爱的权利》那个时期,女性意识是朦胧的、不自觉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极大影响,与时代的改革开放同步同期,然后逐渐清晰起来,处于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是一个很长的嬗变过程。到了21世纪,很多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作品,都已具备了真正自觉的女性意识,比如王安忆的《天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她写了一个大家族的败落,在这期间,女性如何被迫或是必然地担当起了一个家庭的经济责任和重担,最后使女红的绣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了高价值的商品和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这个看似不得已的变化过程,写出了女性如何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天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部女性小说。徐小斌的长篇《羽蛇》,写了三代女人的命运,去年还有一部非常美丽的爱情小说叫《天鹅》,都有清晰的女性意识表达。其他还有铁凝的《玫瑰门》、严歌苓早期的《雌性的草地》、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等,都有深度地表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以及女性与社会的关系。我在2002年出版的《作女》,则是有意识地描述现代女性特立独行的新形态,也是我对于女性文学的一次尝试。现代社会,女性在精神、物质和情感上都已逐渐不再有依赖性和依附性,对男性的依赖和依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比如,迟子建的《晚安玫瑰》书写了一个俄国老太太和中国女子之间的友情,这部中篇小说的鲜明特点,是讲女人之间的自我疗伤、互相的救助和精神安慰,不再是男性来拯救女性,而是希望表达一种女性的自我拯救。所谓女性意识的自觉,我想是指女性希望由自己来掌控命运的强烈意愿,这种自觉应该是一种深层的主动的清醒的自我认识。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部中篇小说叫做《残忍》,写了文革时期的三个男女知青和一个连长。由于这个连长作恶多端、他欺负了两个男生都喜欢的那个女孩,男知青对他进行了审问之后,实在忍无可忍,在北大荒的特殊背景下,茫茫大地荒无人烟,把他活埋了。荒原夏季多雨,过些天草就长起来了,没人发现这个事情,这个连长就这样失踪了。场部下来工作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把失踪变成了“好事”只能说这个连长牺牲了,要追认他为烈士。那个男知青无法忍受这样的谎言,因为他本来是为民除害,怎么坏人反而变成了英雄,一气之下他就去自首了,他宁可去死,也不能让连长成为英雄。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很惨烈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被这两个男知青喜欢的这个女孩,其实在文本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是一个隐身的人物。男知青为她主持正义,把那个连长用暴力杀害了。当这个连长被杀以后,他们把这个真相告诉那个女孩,都希望自己在女孩子面前很有英雄气概,但是这个女孩从那以后就失踪了,她也失踪了,是主动的离开或出走。什么叫做女性意识的自觉性,就是这个女孩不能接受你们男人用暴力的形式来保护我,我不需要这样的拯救,她不接受这种残忍的行为。连长的死看似因她而起,但她是被动地被卷入这种暴力行为的,所以她有权拒绝“英雄”。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探讨人性。但在这个女性人物身上,不自觉地体现出的女性意识的一种自觉,回过头来看,还是挺可贵的,因为它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不是刻意追求的。也就是说女作家写作的时候,不要整天去想着要去写一部伟大的女性主义作品。当女性具备了现代人的意识,尊重生活和自然的基本规律,这种意识就应该生长在自己心里,生长在自己的血肉当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输送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去。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把男作家的作品和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一些对比。男作家笔下,对女性的态度,和女作家是不一样的。他们作品中的男性人物设计,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似乎天下的女人都以崇高美好的爱情的名义,对男人崇拜得死去活来,他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情感上都是非常依赖于男性的。这种情况,到了70后、80后的男作家那里,才开始有所改变。
第二,简单讲一讲女性写作的拓展。我的意思是,要从传统的两性关系,家庭关系进入到女性和社会的关系,女性和历史的关系,女性和人类的关系,而不再是孤立的、悬浮的,应该置身于复杂的、沉重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是有依托的。比如林白的《北去来辞》,就是一次比较明显的拓展,外延伸展到生活的底层。还有严歌苓的《陆范焉识》,残雪近期的短篇小说《尘埃》等等,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残雪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写《尘埃》的感觉,充满了昂扬和叛逆精神,不是局限于女性的自我感觉。我特别要强调王小妮的《1966》,她实际上一个个短篇陆陆续续发表的,2014年终于结辑成书,在今年图书书展中还得了奖,黑色的封面,很压抑很沉重。但她的叙述风格有点像箫红的《呼兰河传》,淡淡的,简约的、有伸展余地和想象空间,文革惨烈的狂风暴雨,在女性眼里,是非政治化的、而是人性的,是日常生活世俗文化人情冷暖的破坏与溃败,完全是女作家的眼光和感觉。她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书写,而是把它放到重新审视文革的层面上。文革这样的历史话题,对女性作家而言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性,王小妮的《1966》值得作为女性写作拓展的分析文本。
第三,就是女性写作的深化,这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其实刚才我讲的几个方面都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刚才美国教授柏棣讲到了自我实际上是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我觉得,所谓“自我”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比如:我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女性怎么认识自己?如何剖析女性自身的弱点?如何克服女性的身份焦虑、性别焦虑…… 总体看女性写作,我认为我们对于生活的沉淀、认知、提炼、创造都还远远不够。经典的产生,重要的条件是时间的孵化,它是一个时间的孵化品。我的长篇小说已经陆续写了近十年,目前正在修改第五稿。一个写作者如果还能对自己感到不满意,我想就应该能够进步。由于我的社会工作比较多,所以写作的进度比较慢,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学到很多,我是一直在往深处走,所以不仅是付出,而是在收获。既艰难却非常有意思,也是女性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
陈骏涛: 我今年七十有九,逼近“八零后”了,是今天到会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这两三年由于思维状态的迟滞,在会议上很少发言。这个会我本来也是不准备发言的,因为从2013年3月我写了关于女性文学的最后一篇文章《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线——关于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话题》(《新文学视野》2013年第3期)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别的文章了,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也所知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了。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但是经不住王红旗女士的执着相邀,还是决定简单地说一点。说实话,这些天,为了这篇发言,还真有点焦虑不安,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何说起。考虑再三,我想还是老老实实地从切身的经历和感受谈起吧。说错的地方,请各位谅解并批评指正!对女性文学做批评研究,不是我的所长,我介入的时间也比较晚,我曾说过,我是这个领域里一名迟到的“票友”,这是大实话。当然,也可以说是一名忠实的“票友”。起因于1994年冬天应邀主编《红辣椒女性文丛》,开始了我的女性文学“票友”的生涯,写了生平第一篇关于女性文学的文章——《红辣椒女性文丛•总序》,曾以《“女性文学”刍议》为题,发表于1995年4月11日《光明日报》的文学专刊上。从那以后的20年来,我读到了不少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女性学者的著作,参加了关于女性文学、关于女性主义、关于性别问题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包括境内的和境外的)总有数十次之多,由此而结识了许多女性朋友,包括女学者和女作家(也包括境内外的)。在坐的各位,包括张抗抗和徐小斌女士,也大都是因此而认识的。还有我的几位女学生,包括因病或因事而未能到会的谭湘、朱育颖,以及今天到会的肖菊蘋。写的这方面的大大小小的文章大概也有数十万字之多,虽然大多是一时一地的应需之作,属于“过眼烟云”之类,但也有一部分是下了点功夫、今天可能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文字,如收入我的文学评论选《从一而终》中的《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沉潜中的行进》等几篇文章,以及选入王红旗主编的《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文选集成》以及其他选本中的《“她世纪”与中国女性写作的走向》等几篇文章。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写作,居然会成为我进入老年期以后的主业之一,使我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使我的自然生命得以再造。十年以前,我在河南开封的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上有一篇发言,题目是《生命的再造与张扬》,说得也都是实话。这篇文章在次年《百花洲》第1期上也发表过。回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的发展历程,我在《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先发表于2004年《职大学报》,后来又与我的学生郭素平做了一个对话,发表于2005年8月《中国女性主义》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中国女性主义从80年代以来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是第一阶段,我把它叫做“中国女性主义的萌生期”,或者说是中国女性再度“浮出历史地表”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是中国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性别意识自觉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主义从萌生到成长的阶段。而从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它仍处于成长期,但却是上个阶段的延伸和发展,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个延伸和发展的阶段中。中国的女性文学和文化,中国的女性主义,从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到如今,已经经历了30余年。面对着许多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包括许多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所做的许多努力,我们现在又应该再做些什么呢?这正是当今许多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些热心于女性文学和文化事业的男性“票友”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会议的组织者提出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女性文学的经典化”,一个是“性别视野和跨界书写”。尽管我本人对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继续学习和思考,一时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来,但我相信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关系到中国女性文学和文化持续发展和提升的问题。我将期待着,同时洗耳恭听各位的精彩发言。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语焉不详,言不及意,请各位多多包涵!谢谢各位!
徐小斌:我执与无执
最近我在做一件貌似与文学不沾边的事,就是受国家开放大学之邀,讲授西方美术史二十讲。但是在备课过程中,我有了很多意外的收获,感悟到了很多之前没有感悟到的东西,我有意讲授了一批同一人格类型的画家,这类画家都是在生前被遮蔽,而在过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后的当代,被研究者们挖掘出来重新研究,获得极高的赞誉,在美术史上占据了极高的地位。这些画家生前有多人都是贫穷落漠的,绝不止是凡高,包括塞尚、卢梭、雷东、等等,他们天才的画作无人问津,无人喝彩,在一个孤寂冷漠的道路上,他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唯一的答案就是“我执”。他就是爱这个,就是真爱。联系到我们的今天,用戴锦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很难再重建‘你们男人’和‘我们女人’的叙述模式,因为‘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勿庸讳言,现在的社会游戏规则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渗透在各个领域。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娱乐节目、真人秀什么的,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所有选秀最后的冠军几乎都是男性,而在网上各大论坛里,在各种言论中也几乎都是女性想如何取悦男性的自轻自贱。这个碎裂如何拼贴,可能我太悲观,我认为几乎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女性如何在这些一个被自然雾霾和人文雾霾双重污染了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坚持纯粹的写作,唯一坚持的动力就是“我执”了,也就是对文学的真爱——把文学当作信仰来爱。除了“我执”,还应“无执”。怎么讲?解释“我执”与“无执”这两个概念,恐怕不会有比女画家狄妃奥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了。

徐小斌 著名作家、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国家一级编剧
现在已经鲜有人知出生于1930年的美国女画家简•狄妃奥(Jay.Defeo)。她曾经集美丽、富有、才华于一身,却在二十九岁那年,自我封闭,画一幅《死亡玫瑰》,画了整整十一年,画得爱人离异,朋友分手,期间曾获顶级策展人之邀参加万人期待的重要画展,却被她以作品尚未完成而拒绝;十一年后作品完成,上面的颜料堆积重达三千多磅,合一顿多重,由八个装卸工破窗而入,把这幅与其叫绘画不如叫雕塑的巨幅作品搬出(后此举被一些画评家譬喻为阴道切开术),而这时,巴洛克时代已经变成了POP时代,此画成为摆在旧金山艺术教室中长期被泼洒咖啡、按熄烟头的废品,而那些由艺术家堆积的过于厚重的颜料,也随着时日一块块崩塌。对此,狄妃奥只是淡淡地说:人类会消亡,艺术也会消亡。就这样,她精心建构的世界却被忽略,被遗忘,被淹没,不是她的错,而是时代的变换——但她并不关心大众的接受度与评价,更无意于去争锋邀宠,哭爹喊娘,歇斯底里,或者变成喋喋不休的祥林嫂,拦路告状的秦香莲,或者像我们伟大的凡高那样伤筋动骨(毫无贬低凡高之意,凡高同样是我深爱的艺术家)——而是平静、沉默地接受现实,因了这平静与沉默,她的接受显得格外高贵——可谓“无执”。提到高贵这两个字,似乎已经完全变味了。小时候读的书,譬如《前夜》里那个坚忍的保加利亚革命者,譬如那些不屈的十二月党人,都是我心中对于高贵二字的代名词,所谓贵族精神,与有钱没钱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在如今都要解释一番,也是很可悲了。譬如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十有九个都被所谓“成功学”毒害,因为看到了所谓出名带来的巨大利益,但是按照贵族精神,出名是一件可耻的事,典型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在发明了相对论之后,瞬间爆红,得到无数的邀约,他在数月之后就感到羞愧难当,赶紧躲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因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贵族们都是以出名为耻的。但是现在最可怕的是,已经有很多人不知道高贵为何物了,举一个最近的例子:锵锵三人行最近一期中,窦文涛就讲到昂山素季,说到她作出的巨大牺牲,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盘算的。”当时周轶君就说: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为自己的信仰殉道的,并没有个人的盘算,然后窦文涛就说,不要相信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其实现在持窦文涛观点的人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怎么解释圣雄甘地?怎么解释马丁•路德金?怎么解释耶酥•基督和释迦牟尼呢?高贵的精神不但被淹没,还不被相信了,这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哀。
其实,那种至死不泯的高贵精神也是一种“执”。既是“我执”也是“无执”。
在作客“凤凰名人面对面”时,当许戈辉问道:“你写得这么好,可是我之前不知道你”时,我对她讲了狄妃奥的故事。在“我执”与“无执”这一点上,我与这位女画家很是相通,甚至,比她更为极端。在文字上,我会对自己非常严苛,每一部小说都是自我折磨充满疼痛的产品,我会深度迷恋,忘记身处的世界,可谓“我执”;然而作品完成后,我精心建构的隐喻世界常常很难被识破,但我真的不大关心结果如何——可谓“无执”。佛说:娑婆无执。但实话,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譬如在九十年代我的一系列作品出来之后,《羽蛇》、《双鱼星座》《迷幻花园》《末日的阳光》等等,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个也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动力,但是进入2000年中期之后,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对我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好像是从我在2006年在《十月》发表的小说《别人》开始的,当时我还有博客,我的博客上关于这篇小说有七万余条留言,可无论是《小说选刊》还是《小说月报》都没有转载,当时有朋友提醒我说你电话一下某某,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他现在升了,你得表示一下对他的尊重。但是我始终没打这个电话。而《小说月报》的主编后来看了这篇小说之后,专门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小说月报》漏选的所谓‘遗珠之恨’,《别人》在这本书里是头条,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所谓遗珠之恨,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更有甚者,有一著名杂志主编私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小说给我?这篇小说应当拿鲁奖。”——文学环境的变味儿也许早就开始了,但是愚钝如我,直到那时才尖锐地感觉到了变化。也正因如此,有时我觉得自己走得非常孤独,也非常艰难,有时也会感觉到不公平。但是我终于明白,这就是当社会变了,而人依然保持他的完整人格的时候,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代价就是不断丧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乏真正关注我的人,红旗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位,她曾经在我的长篇《炼狱之花》和《天鹅》之后,在中国网为我做了非常精彩的长篇访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红旗和以她为代表的女性文化研究都有着很高的水准,对她我一直心存感激。以女画家的故事收尾:九十年代,当《死亡玫瑰》已经囿积二十年之久,画家亦早已故去,纽约的一家著名美术馆终于以高价购买了这幅画——重量、规模、低彩度,向心形式,这一切成为画界独一无二的概念,只有站立在画作面前,当阳光掠过,才能深感此画的神秘动人之美。艺术比生命更长久。最奇异的是狄妃奥生前做过一个异梦:她梦见自己死后转世投胎成为另一个人,她漫步在一座美术馆,看到那里正在展出她的《玫瑰》,一个人,正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着她的画作,她走过去,轻轻地对那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画”。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谢谢大家。
柏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念问题二十世纪初至今,女性文学在中国有两次兴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中出现的第一波女性文学运动随着革命文学的高涨而衰落。第二波女性文学运动的出现恰逢革命文学的消退。在二十一世纪初,以“私人空间”“女性意识”为特征的第二波已接近尾声。正因为女性文学是现代的产物,女性文学批评的中的基本概念则必然地含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现代特征。而对历史性的关注正是女性文学批评领域所缺乏的所忽略了的。我将通过对“女性”、“社会性别”和“本土化”这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的讨论说明,这些概念的发生、发展和内涵的演变同同全球化的进程息息相关。

段炼:米柯•鲍尔的学术身份
米柯•鲍尔于1946年生于荷兰一个犹太家庭,她是今日享誉国际的视觉文化学者,其研究所涉甚广,横跨视觉艺术、文学理论、犹太历史、圣经考古、人类学、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等领域,同时她也从事艺术创作和电影制作,而主要成就则在于图像符号学和文学叙事学的研究,后者有中译本行世。米柯•鲍尔现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文艺理论教授,也在欧洲和美国多所大学任职。最近二十多年她对西方学界的视觉文化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1993年她与其他学者共同发起创办了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院,也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与其他学者发起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视觉文化研究博士点。关于米柯•鲍尔在各学术领域的著述,读者可在其官网获取详细资料,关于她的学术观点和方法,英国当代著名学者布莱逊为她写过学术小传,可供参考。

段 炼 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教授、中文部负责人、资深文艺评论家
卓慧臻:中西女性战争书写——从伍尔夫与张爱玲谈起战争是文学中经常被书写的内容,两次世界大战特殊灾难和军事性的对阵布局,触发世界诸多变化,使得文学家使用意识流的手法和面对内在世界的形式来陈述个人世界。本文以著名小说家伍尔夫写于一战的《达洛维夫人》为主,并比较张爱玲写于二战的《倾城之恋》,试图勾勒女作家如何呈现战争生活,个人及群体如何对应战争带来的转变。

卓慧臻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比较文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