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与会嘉宾
《合欢牡丹》问世
江岚简介:江岚,教育技术学硕士,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华文女作家。现居美国, 从事国际汉语教学、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与传播的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中文版 2009,2011) 。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各类体裁作品曾先后多次获奖并被收录于海外华人作家文集计39种。出版长篇小说《合欢牡丹》(2016),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2009),报告文学专辑《旅美生涯:讲述华裔》(2009)。“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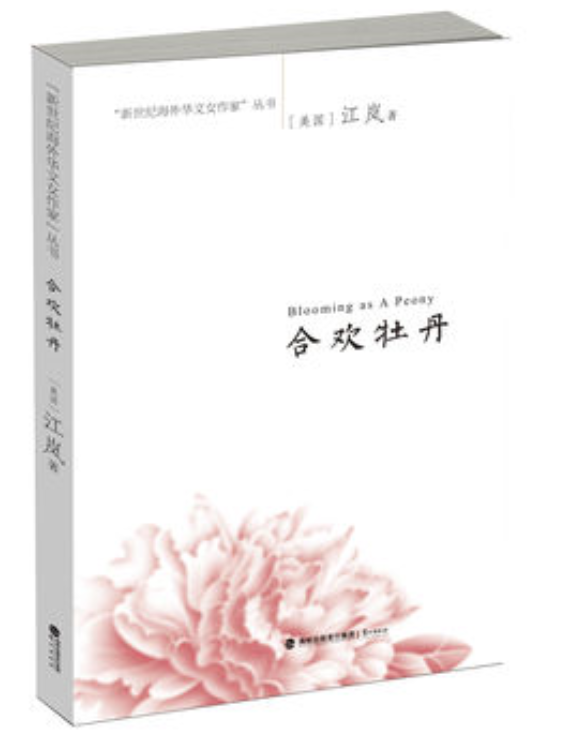
王红旗:祝贺你主编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和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由鹭江出版社出版问世。这是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一件盛事,作为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女性文学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代表国内的学者朋友向诸位姐妹表示真诚的祝贺。
收到鹭江出版社快递来的全套丛书之后,我马上拆开包装,坐在沙发上一本一本拜读起来。感受最深的是,这几位女作家,她们不仅在创作方面个个风头正健,而且,用各自“绽放的灵魂风景”,标示出海外华人知识女性精神追求、生命之境的新状态。如果从世界华文女性文学史的角度看,表现出海外华人女性自我生命经验叙事的独特性魅力,超越性意义。请谈谈您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江 岚: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圈里,以女性作家占压倒性多数。她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但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的文本尚不足以体现她们整体性的创作成果。为进一步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满足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文本需求,由鹭江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笪林华策划,召集在海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批女作家,编辑出版“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希望藉此激励海外女作家们在创作热情之外,更主动更积极地去寻求去承担她们在海外女性文学创作上的使命;同时向国内学界成序列地呈现海外女性文学现阶段的格局,以推动学界、研究界和创作者间良性互动的局面,共同促进汉语言文学超越地域、超越国别、超越种族的繁荣与发展。今年5月推出的第一期共六册,包括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散文集一部。接下来的15册计划分三期在2016年下半年和2017年初相继推出。

与会嘉宾
精神生命:悬崖→突围→重生
王红旗:你怀揣10年酝酿,数易其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所讲述的这群以不同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国知识女性,无论是随同丈夫出国留学深造的陪读妻子,还是自己出国读硕士、博士的女研究生,她们都是有着“生活真实”的生命个体,其中蕴含着姐妹们的生命体验、精神气质,仿佛心有灵犀,可亲可感。我把她们誉为“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如小说中的沈玉翎、王涓涓、方若施、肖瑀、韩悦等,虽然她们的生存境遇不同,但是她们面临的困境,不在于社会物质层面,而在于妻子与情人的家庭情感角色,真正把她们逼到“悬崖”的,是精神层面渴望“真爱”而不得的灵魂之痛。请问,你是如何在日常生活里捕捉到海外华人女性这种“痛”的?这种“痛”对女性生命意味着是什么?
江 岚:您提到的这种“痛”,客观上说不是我“捕捉”到的,而是身边的女性让我“看见”的。男女之间,惟有一种很纯粹很纯洁,不带有太多客观附加条件的感情,才能被理解为“爱情”。从前以为追求爱情只是青春的事,后来才渐渐明白,对这种爱情的渴望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可以因某个合适的契机在任何年龄段发生。问题是爱情自身感性的,不稳定的自然属性,与生活现实中理性的、规则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现实的理性模式越来越趋于固定,爱情的自然属性却不会改变,于是二者之间的冲突便越来越难以调和。女性天生的敏感纤细特别容易被这一对矛盾冲突的结果所刺痛,矛盾越尖锐,冲突越激烈,她们内心的痛感就越深重。
王红旗:但是作品中的女性,并没有因“痛”而沉默下去,而是不约而同地、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挣扎着“突围”。其实,或许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能否突围出这座跨文化的情感围城,是否能够打开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然而,根植于内心、流淌在血液里的“原乡”记忆——牡丹的精神,成为她们在“他乡”自我认识与反省,积蓄勇气与力量的文化母乳。因此“合欢牡丹”是小说的内在灵魂意象,更是人物精神生命的象征。请谈谈你最初的构思过程,怎么就想到了“合欢牡丹”?
江 岚:世间万物,似乎总有些造化生成的某种特殊关联。我从小喜欢植物,总觉得万千植物就像万千秉性各异、风格不同的人。最初了解到牡丹在北美的种植历史及其生长特性,马上直觉地联想到身边那些华人女性新移民。她们抛别故土的孤独,在陌生土地上扎根的顽强,以及站稳脚跟之后的恣意绽放,和被裸根移植的牡丹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题记用的唐代诗人徐仲雅的残句“平分造化双苞去,拆破春风两面开”,原意形容的是一种一萼两朵,花开双色两面的名贵牡丹品种,叫做“合欢牡丹”。我借过来比喻我的女主人公们文化背景的双重性,生命表现的双重性,包括她们对待自身精神、心理与情感需求的态度的双重性。

王红旗:我认为这里所展示的,不仅是“合欢牡丹”“平分造化”的自然之美,而且寄托了你所要表达的男女平等之意、和谐理想之境,隐喻海外华人知识女性,在遭遇生存困境、婚变寒霜那一刻,其性别自信、独立意识依然坚韧不屈生长……,反映出知识女性抛掉“依赖”与不自信的樊篱之后,生命的创造潜力、智慧勇气就会无限绽放,就会走出围城,超越自我,获得新生命。这才是海外华人知识女性像牡丹一样,最有价值的新气质,最具魅力的新风度,最富内涵的新精神。因此,你塑造的女性在异国复杂的生命体验中,锤炼得自信坚强、优雅敏捷、才华横溢。甚至可以说她们体现出的新特质,会让世界重新认识华人知识女性形象。这是你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贡献。
江 岚:谢谢。我的女主人公们都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带着较高的母文化素养和强烈的进取心,她们离家去国,为了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抉择;落地之后,她们与信息时代同时成长,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模式与层面比前代更多元化,她们在自我实现的奋斗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也都是主动的。作为一个整体,她们在异域土地上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和文化心理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而构建出女性新移民这种群体形象的社会大背景,是这一代人总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是中美之间各个层面交流的深化扩展,也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王红旗:对,性别自信与精神追求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是你笔下女性形象生存智慧的新特质。小说可以说是你生活的经验事件的串联,你所书写的四、五对家庭,其中两位知识女性跟你当年做“陪读妻子”的处境很相似。因此,你能够由她们的日常生活进入到她们的灵魂深处,对这群海外华人知识女性生活之困、情爱之殇、内心挣扎,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反思与批判,非常尖锐而深刻。你曾说过,你笔下的这群女性,不仅有身边周围的生活原型,也有自己的影子。在特殊的生存境遇之下,多样性的婚恋观、家庭观、被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形神毕现。其中,沈玉翎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形象。
江 岚: 20多年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叫《爱情故事》,描写的一个“陪读妻子”在旅美初期对新环境无所适从,对爱情走入婚姻之后的平淡无法适应,这一切最终导致她的出轨。而出轨之后,所有的矛盾和压力并未解决或缓和,她却必须面对道德原则的自我拷问。这个女主角可以说是沈玉翎的雏形。“陪读”和“留学”最大的不同,在于陪读妻子们在决定为陪丈夫读书而离乡背井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选择了放弃自我。所以到了异域的土地上,面对生存的压力,她们要跨越种种客观限制,重新寻回自己,然后准确定位自己,最后再实现自己的过程就更加艰难。当然“出轨”肯定不是她们每个人的必然经历,但在旅美初期,她们自我意识的被屏蔽,精神上的被孤立,情感上的被荒芜却相仿佛。
王红旗:这个“放弃自我”很透彻。沈玉翎作为“陪读妻子”,乐观自立,勤奋好学,刚到美国“一切从头学起”,打短工贴补家用,练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口语,考入护理学院读书,最后不仅被老年护养公寓聘用,还做华文媒体的兼职摄影记者。她的丈夫秦中恺,则一直固定在他的实验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当初情感很好的一对夫妻,变成了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即使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也没有了真正的心灵交会。表面看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实际上是揭示当夫妻各按自己轨道行事,“忙碌”形成一种习惯,生活里拥有的爱会一点点被磨损,甚至丢失。这样的家庭生活节奏、婚姻情感状态,让沈玉翎感觉到烦闷而乏味。更重要的是沈玉翎的自我精神生命成长,她为了爱情可以“放弃自我”,为了家庭可以吃苦受累,担当了作为妻子的责任,秦中恺却忽略了她的情感。
江 岚:结婚这件事情,作为人生情感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对男人而言,标志着攻城略地的任务已经完成,激情随之归于平淡,他从此可以全心经营自己和“家庭”,而不再花什么心思去经营“爱情”了。可女人是不一样的。她们“自我”的情感需求独立于“家庭”角色之外,不会因这个节点而改变,更不会在这个节点上终结。她们不仅需要“被爱”,更需要这种“被爱”的主观感受在日常的生活里不断被强调、反复被确认。
王红旗:就像方若施所言“可见女人再聪明、再能干,专业上再出色,最终想要的也只有一样。爱情真是女人身上的死穴,她们需要去爱,更需要被爱。”秦中恺在夫妻情感伦理上,缺乏精神成长的认同,沈玉翎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小姑娘,但实际上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她渴望灵与肉相结合的爱,渴望精神的相互滋养,渴望职业共谋的支持。这些渴望随着她的年龄阅历一起增长,秦中恺跟不上她的步伐了。尤其女人中年的成长比男人要快,甚至女人永远都在成长。
江 岚:秦中恺的观念里,男人在婚姻里的责任是为女人提供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并不懂得,女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安全感”,更需要精神上情感上的“安全感”。二者其实并非相互排他,完全可以并存并行,问题是他意识不到。更可悲之处在于,往往在物质层面的“安全”之后,女人精神和情感上的“不安全”反而会被格外凸显出来。
王红旗:关键是,秦中凯作为丈夫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才是中国男性的“死穴”。女性渴望爱与被爱,是人性本然。其实,结缔婚姻是夫妻相互尊重学习爱的一种方式,家庭日常生活是一个爱人与被爱的生命课堂。现代人把爱看得太表面化了。你把沈玉翎为寻爱而红杏出墙,写得很出彩。她在采访时遇到亚裔知名企业家刘家鼎,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不能自已,对这位有妇之夫、年长自己三十岁,如父亲般的男人,喊出了“我爱你”而坠入爱河。小说中写到他们二人:“很刻意地合力按动一个看不见的遥控器,将那个小小套房用无数幅粉红色的布幔与世界隔开。他们沉醉在这布幔之内的幻境里,在没有生活琐事烦扰,没有外界约束的状态下,体验着一种更接近于其本质意义上的,纯粹的两情相悦”。任由他把自己从“一个平凡普通的少妇”还原成了“一个被娇纵被宠爱的小女人”。你运用这种超越世俗与年龄的爱情体验,想要表达海外华人知识女性怎样深层心理?
江 岚:其一,玉翎对刘家鼎感情的发生,没有基础,没有过渡,甚至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性。她就是在情感被荒芜的状态里闭门造车,给自己酿出一杯自我陶醉的酒。她刻意地、努力地在这段非份的感情里去体验一种自我的原始回归与重新塑造,却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这只能是饮鸩止渴。其二,对青春韶华的追恋,是沈玉翎出轨的导火索。而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长期缺席。其内心深处潜在的“恋父情结”,又构成她对刘家鼎情感的复杂性。其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规范,从未在她心里泯灭,却无法抵御情感的澎湃冲击。因为她长期被荒芜、被忽略、被压抑的情绪需要一个安放之处。
王红旗:哪怕是“暂时的”。她的童年生活给她心理留下一个男性缺席的“空洞”,也孕育了她性格中的坚韧。因此作品中当朋友说她,男人的事情你应该让男人去干,她突然觉得什么是男人该干的事,我不知道,所有事都是女人干的啊。因此,刘家鼎男性的,“长者”式的关怀和体贴,一下子激活了她深藏于心底的“恋父情结”,对其产生了一种对父亲对情人的复杂情感,而没有任何物质上“被保障”的要求。也就是说,沈玉翎形象的塑造拒绝“空洞”、“物化”的情人角色,挣脱了欲望物质、世俗道德的羁绊,达到了一种呼之欲出、超凡脱俗的艺术与精神境界。
江 岚:这里必须回到我前面提到过的,关于“爱情”的定义。沈玉翎是这种爱情的追随者和具体实践者。问题是,她遇到刘家鼎的时间完全不对,致使这份爱情可以发生却根本不可能被完成。
王红旗:实际上男人骨子里会把女人看为物,这一点在东西方文化里颇为相似。刘家鼎得知自己身患绝症,还是要给沈玉翎留一座房产。这个细节揭示人物心理很真实。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她以后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是为了爱她,如果从更深层心理去看,会觉得刘家鼎的骨子里还仍然是居高的、占有的,我爱的女人得依靠我,我死了之后还得依靠我。
江 岚:对,我不能陪着她到老,所以我就得保证她衣食无忧,他说的就是,她不会因为爱过我而后悔。
王红旗:沈玉翎表面上很独立,内心却十分软弱。“送房子”的事件一出现,“物质”与“精神”就分离了。刘家鼎认为她再生了“我的生命”,沈玉翎全身心的投入这份“一无恩怨的纠葛,二无利益的牵扯,三无名份的约束”的纯粹爱情,就已经降落到“物”的层面、交换的层面了。你亲手搭建了这个爱巢,却有意再把它推倒,是意味深长的。
江 岚:是的。沈玉翎出轨的直接推动力,是精神与情感的饥渴。然而她和刘家鼎之间缺乏产生共同话题的基础,自始至终没有实质上的精神层面的交流,他们沉迷于其中的所谓“契合”,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物理反应而已。所以,她最后所能够得到的,其实只有幻灭。
王红旗:还有学习英美文学专业的王涓涓,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丈夫是自己父亲的高材生。被父母在“一种休眠的状态下被移植”进不满意的婚姻,以陪读身份随夫迁徙美国。这位“陪读妻子”与沈玉翎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对环境恐惧,对丈夫依赖,她放弃读书与工作的机会,甘愿做“全职太太”,传统的“贤妻良母”。然而,丈夫却以经济拮据为由,时常对她埋怨、侮辱与责骂,甚至施加暴力,她被逼到悬崖之后梦醒,主动与丈夫提出离婚,在姐妹们的热心帮助下走向独立。从沈玉翎与王涓涓的两种不幸婚姻来看,你对“陪读妻子”生存现状的考察是双向的。前者沈玉翎因双重角色的过分“忙碌”,后者王涓涓因物质与精神的“依赖”,都将自己置于“无爱”婚姻的尴尬、危险境地。最终一个主动去追逐情感的自我而回归家庭,一个主动离婚后生成独立自我。从自我迷途到精神新生,你对女性内在灵魂不同程度的经验反思,颇具历史与现实文化意义。
江 岚:我最后通过沈玉翎的眼睛评价王涓涓:若不是曾经被逼到“悬崖”,怎么会这样。舒婷很早以前就在她有名的诗作《致橡树》里形象地描述过,女人应该“作为树的形象”和男人并肩站在一起,这是两性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女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藤,没有独立人格,缺乏自我积累,那么最后的结局若不是树被藤缠死,就是藤自己营养不良而亡。在这部小说里,沈玉翎和方若施是两棵树,王涓涓是藤,韩悦则介于二者之间。
王红旗:这个比喻很形象、贴切。韩悦拿着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她不是“陪读妻子”,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谋发展的过程,看起来也一帆风顺。可经济独立并不等于精神的独立。
江 岚:是。她对丈夫的情感依赖不明显,却更深刻。所以她在捕捉到丈夫出轨的事实之后,会容忍他,甚至主动原谅他的背叛。小说里,赵明中和刘家鼎这两个男人都婚外另有情,性质却完全不同。相对于刘家鼎的“重获新生”,赵明中不过是“一晌贪欢”。韩悦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所以能够以一个高级知识女性的智慧,冷静地、从容地去化解婚姻的危机。
王红旗:男人还没有准备,好女人已经解放了。当代社会仍是一个男权文化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无论传统与现代文化,都给中国男人带来一种“宠儿”的优势心理。尤其是在两性关系方面,中国的知识男性根本就没有走出“传统怪圈”。他们对“阉割”式的束缚、压抑,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江 岚:一个知识女性想要的精神爱情及其安全感,不是男人能给予她们的,而是她们自己争取来的。我就是想写这样一种现象。
王红旗:你揭开的就是这种现象。这是女人的悲剧,也是男人的悲剧。沈玉翎劝王娟娟时说,靠谁也靠不住,女人只能靠自己。所以你得自我独立,你的精神,你的物质,只能靠自己。
江 岚:她不断地在说这个话,方若施也说这个话,说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都要靠自己,可是在行为的过程当中,她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想去寻找一个男性来依靠。
王红旗:这就是女性情感世界所面临的一个现代性悖论。人性本然需要灵魂相依,精神需要共化而生,原本就是建立在个体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夫妻关系原本也应该是平等的亲密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夫妻双方理应是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性生活的亲密伙伴。中国人历来把夫妻关系的美好理想比喻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这是从“母神文明”时代传承数万年的精神文化遗产。但是,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观念,以不断完备的等级制度束缚女性并内化于心,使男性位高权重、女性位卑势弱,逐步演化为天经地义。即使在当下仍然把剩女、女汉子、女强人的歧视之冕强加给有知识、有智慧的女性。有些女性也有意识无意识地受到影响,异化到自我独立的精神光华褪色殆尽。因此,我觉得女性真正的精神独立和解放,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啊。并且需要男性的觉醒。这一点你如何认识?
江 岚:今天的知识女性,是一个成熟的自强的稳健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口之众多,专业领域之广阔,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之丰厚,远非前代的女性们所能够想象。可正如您所提到的,男人并没有与女人并肩前进,同步觉醒,还做不到以平等的眼光正视我们的生命体验,接受我们的文化经验。但女性在生活实践中跨越伦理陷阱、逻辑陷阱,用高品质的审美和爱情方式、生活方式,去勾画女性理想的人生图景的步履不会停止。
王红旗:这让我想起了小说开始的场景,在那个中午,人物一出场你就把沈玉翎和方若施抛在曼哈顿的大街上。这个“抛”,是三重身份上的“抛”,文化身份、社会身份、情感身份意义上的“抛”。她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有理想追求,这个理想也被“抛”了。尽管她们可以说是海外华人当中的精英女性,但是她们在情感上都是“空”的。这样的生活画面,留给人更丰富的沉思。揭示出女性全面发展与精神解放,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情,更需要各种政策制度的支持、文化观念的改变。请解释你为何要这样开篇?
江 岚:首先是叙述的需要,交代她们的身份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在异邦的生存状态。其次也想要通过她们的对话,表现出她们在脱离了母文化圈和原乡生活圈之后,客观上更加独立,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以及同时主观上也更加孤寂的文化心理。王红旗:这个被“抛”的出场方式,更展示出人物独立自由的心境。方若施被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女强人”的形象,美丽聪慧,事业成功,经济独立,内心却充满浪漫主义的爱情梦想,渴望“爱”与“被爱”。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对象孟繁星,你却没有让她的爱情故事得到“圆满”结局。江 岚:在小说里,方若施的方方面面都是王涓涓的鲜明对比。王涓涓是初恋受挫之后选择远嫁逃离,方若施是为实现个人奋斗的理想一直待字闺中。孟繁星是她迟到的初恋,除了他外在的,客观的条件之外,她看不到孟繁星的内心,也进不去。到了这个年龄,她内心再渴望再向往,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追求浪漫爱情的能力,她不敢付出不肯付出,就必然不会得到。她的理性已经被锻炼得时时处处要超越感性、压抑感情。
王红旗:这样看起来,沈玉翎和韩悦又是一对彼此参照。沈玉翎是自己红杏出墙,韩悦则要面对丈夫的出轨。
江 岚:她们虽然从相似的起点出发,性格是不同的,生活际遇自然也不同,但都有知识有见地有勇气,敢想敢做,敢做敢当。原乡的记忆让她们留恋,却不构成束缚;异质文化的冲击让她们警醒,却不形成障碍。她们用自己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以同样回旋往复的姿势,去探索更接近于理想的个体的生命建构。
王红旗:这是一种性别自信、民族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下,汲取人类不同文化的精华,积累内在自我能量,才能走向理想的生命之境。就像王涓涓所说的,“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似乎与北美的气候条件有些奇妙的亲缘,不大招惹小动物骚扰,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一旦扎下根,或迟或早必定开出‘一枝红艳露凝香’”。我认为,这是海外华人女性一种自信的。

与会嘉宾
现实生活:“陪读妻子”→作家→教授
王红旗:在我的印象里,您是一个学院派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学者式的作家。一方面您是美国威廉.柏特森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研究古典诗歌。另一方面您多年来坚持用母语写作散文、小说,您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江 岚: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处理,就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从小喜欢写作,到美国以后首先是受乡愁的挤迫,一有空就坐下来写。后来写作渐渐成为一种自然的习惯。不管今天多忙,反正总要坐在那里写,不管能写出多少写出些什么,也还是要写。如果好几天都不能够去写,我会变得很容易烦躁,容易心虚,觉得自己该干的事都没干。也许坐在书桌前一两个小时最多只写了一百个字,可这一两个小时是我必须要保有的私人的空间。
王红旗:这是不是因为您从小就特别喜欢写作?是不是家学的影响或者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
江 岚:更多的是遗传基因的影响吧。家父虽然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一辈子从事文艺美学研究,起初却不愿意让我跟文字打交道,他想让我去学理工科。可我实在没有那个天赋,到最后也还是绕回到文学这条路上来了。我从小跟着祖父母、外祖父母长大,两边都是一大家子人。那个时候虽然说物质生活的条件非常有限,我却是一个被很多很多爱包裹着养大的孩子。我祖父写得一笔好字。经常把家里的废报纸以及所有能找到的废纸拿来练字。先用钢笔,再用毛笔在同样一张纸上正反两面写,全是唐诗宋词。他一边写,我一边似懂非懂地跟着他念。这算是我最初接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吧。
王红旗:原来,奶奶爷爷从小对心性培养,习惯的养成,在有意无意当中传授给您一种通过诵读对诗词的理解能力,培养了你对古诗词的喜爱,不知不觉成为你生命记忆的一部分。而且,你儿时对古诗词的记忆,对你的“唐诗西传”研究都有很大帮助。这真实是一个机缘。
江 岚:是。我祖父也喜欢喝茶。没什么好茶叶,每天照样用紫砂茶壶郑重其事地泡。还有我祖母永远一丝不乱的头发,我外祖母一年四季种的那些菜,我姑姑她们用毛线编织用丝线刺绣的衣服,是贯穿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王红旗:这种节俭朴素、不放弃的生活习惯培养,后来形成了你一种看待人生的态度,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生活有多苦,你都不至于绝望。其实,你在小说里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有这样的影子。我觉得对一个人心灵成长而言,儿时这种爱的温暖记忆是一种精神养分,会滋养相伴你一生。你是何时去美国随丈夫陪读的?
江 岚:20世纪90年代初。起初心里以为陪他读完学位我们就回来了,后来才渐渐明白,留学生们轻易回不来。于是只好和身边其他的陪读妻子们一样,边打工边学英文,后来就工作了,在一位犹太老太太的公司里做服装进出口。几年后因为有了孩子,就把这份工作辞了。后来我决定去读书,考进了里海大学教育学院。拿到硕士学位以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给美洲银行培训部做课程设计。等有了老二,就又呆在家里了。这时候,美国的“汉语热”刚兴起。我因为机缘巧合,进入圣彼得大学的语言文学系教汉语。
王红旗:会说汉语与会教授外国人学汉语,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吧?
江 岚:是。我并没有汉语言的专业知识基础,只好一边教一边自学。读硕士期间的那些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系统训练这时候很管用,让我能够用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讲解汉语的语法现象和语用知识。后来系里决定扩展汉语课程的设置,主任说我应该去读一个博士学位。我也喜欢教书,觉得今后大概是要在这一行里做下去的了,应该加强自己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样进入苏州大学文学院,师从罗时进教授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学位。
王红旗:《唐诗西传史论》就是在你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学术成果吧。这部专著以很独特的视角,奠定了你在汉学西传学术方面的位置,为当代“中学西进”做出了你的贡献。
江 岚:这首先要归功于罗时进教授的学术眼光。他给我定下了一个很适合我自身的情况,又有许多东西可以开掘的研究领域。家父在我整理资料做论文的过程当中也给了我很多提点。没有他们的鼓励、信任和指导,不会有后来的成果。
王红旗:拜读你的《唐诗西传史论》,可以发现你在爬梳古代和近代唐诗向西方传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事件,都是你自己从史料中一点一点挖掘出来的。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唐诗西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西方是从哪些方面来接受我们的文化的?
江 岚:唐诗的英译与西传,是经由那些认识到了唐诗之美的英美汉学家们不懈努力,一步步打开局面,被西方世界所了解、所接受,进而去学习去化用。汉学家们对唐诗真诚而充满善意的阐释,对中华传统文化独特性和独立性的认同,以及为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共识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令人感佩。这个事实反过来又证明,以唐诗为典型代表的中华传统诗学,有着长盛不衰的亮色底蕴,而这个底蕴是能够跨越种族、语言、文化的障碍,被全人类所认识与接受的。
王红旗:当你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之后,你发现对你自己的震撼是什么?
江 岚:我觉得我以及我的后代,在融入美国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必对自身的血脉传承妄自菲薄,不必处心积虑地扭曲自己以迎合西方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土地上,我们就是华人,秉承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气质,站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喝中国茶,穿中国旗袍,讲中国故事。
王红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种发现对你的人生或者对你以前受的教育,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力量,甚至能够寻找到人类在精神层面的同构性,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发现,与外面如何讲是不一样的,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在《合欢牡丹》的结尾处,你运用托物言志的古典式表达,把这种性别自信、民族自信与人类意识推演到了高潮。“那经历风霜雨雪的锤炼之后,用时间和生命蕴蓄出来的成熟、丰满的芳华尽情招展,挺立着从容端丽,仪态万方。而且还有香,不是玫瑰的浓郁,也不是茉莉的恬淡,微风过处挟带起的丝丝缕缕,仿佛无处不在……”。当然,这也是小说精神脉络的高峰,更是海外华人女性理想生命之境的隐喻。你借助方若施与孟繁星的订婚宴,邀请作品中所有人物各怀心思纷纷亮相。“以阿施和孟繁星为中心,玉翎挽着秦中恺的臂弯,李文韬拥着涓涓的肩膀,韩悦夹在赵明中和章明之间,几个人站在牡丹花丛前面,迎着初夏午后的阳光,镜头里的笑容璀璨明媚,没有一丝阴霾”。这个“开放性”、“在路上”的尾声,不仅勾画出一幅充满爱与友情的华人“在地”生活真实之景,而且蕴含着一种重构性别伦理、婚姻关系的美好愿望,所生成的“可能性”的未来华人世界。不仅暗示“太阳光下”华人女性命运不可预知的变数与悬疑,而且暗喻某种人类文明物质与精神进化的某种规律性。因为,人类曾以百万次地面对这种经验的现实,每一次跋涉未知都心存焦虑、步履艰难,每一次爬上坦途都坚信超越、风景无限。
江 岚:的确,方若施与孟繁星的婚姻前景,在第十六章一开始纽约同性恋骄傲大游行里,我特意用了比较暧昧的伏笔。让孟繁星紧紧依偎在“新近崭露头角、有华裔血统的服装设计师卡尔斯•王”的身边,沈玉翎立刻就认为他是同性恋,而更成熟更老练的刘家鼎却不以为然。到后来写到这些服装设计师们出席订婚宴,我又很刻意地通过衣着描写暗示他们性取向的暧昧,强调沈玉翎的判断的合理性,同时也再一次暗示方若施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清一色都是男人,身上却不像其他男宾一律穿黑色,而有铁锈色、奶油色、宝蓝色、亮胡桃色等等,甚至还有穿银灰色配粉红背心的,凑在一起十分显眼”。其实,我在强调社会的、意识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多元变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王红旗:如果从女性生存的角度看,正牌单身“女强人” 方若施订婚了;辛苦创办华文媒体的肖瑀也苦尽甘来;沈玉翎红杏出墙之后回归家庭,王涓涓从全职家庭主妇成了专业美甲师,最年轻的韩悦也用智慧化解了婚姻的危机。应该说她们是有能力把“高处不胜寒”化为 “高出不胜美”的知识精英女性。她们在欧风美雨的大浪淘沙中“落地生根”,把工作事业、日常生活与婚姻情感都经营得风生水起。此时,她们均有自己的爱人相伴,在异乡也似“故乡”的天空下,生命像牡丹绽放得姹紫嫣红,迸发出无限的精神能量。
江 岚: 是的,我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同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她们之间的鲜明个性是相映成辉的,友谊是温暖灵魂的,相互搀扶成长的。面对种种生存困境,“突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出走”成为突围的另一种方式。但是,精神成长确实殊途同归的。
王红旗:对。她们独立奋起的勇气,不屈坚韧的意志,智慧强大的内在自我,实现生命价值理想的精神,是有共同灵魂底色的。此人此时此景,你的理想自我、海外华人女性的理想自我,与牡丹的国色天香都融合在一起,构成绝妙的诗意景致。你把华人女性不同体验的日常生活碎片,连缀成一种超越自我生命的大爱而延伸敞开,引领每个人去攀登灵魂的高原,去采摘精神的花朵——牡丹。牡丹成为一种女性独立精神的象征,成为女性生命的信仰之花、精神之花,达到了“思接千载”的跨文化、跨时空的审美共鸣。谢谢你!你的小说给我们带来对女性内在精神力量的思考。
本期信息
嘉宾介绍
|
|
精彩片段
活动预告及报名
联系方式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王红旗
助理 周显波
责任编辑 蔡晓娟 王琳
联系电话:888280514
电子邮箱:female@china.org.cn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联合出品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联合出品








